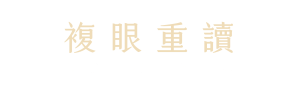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蔡怡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這篇文章的起點,要從我一位朋友H的經驗講起。H幾年前懷了孩子,產檢時發現胎兒的腦部發育情形有問題,但無法明確得知問題的嚴重性,例如對出生後各方面發展的影響。得知產檢結果的H與丈夫馬上面臨是否生下孩子的困難抉擇之中。經歷一番思考,H與丈夫決定生下孩子,但卻面臨身旁一些人對此決定的種種質疑,包括養育一個不健全的孩子所面臨的沈重負擔、對家庭的衝擊、將一個有所殘缺的生命帶來世界對社會帶來的額外負擔,以及讓殘缺的生命痛苦地活在世界上有何意義等問題。一位殘疾兒的生命從出生的那刻起就與難以承受的重擔勾連,包括一輩子依賴他人的照顧,也要在許多疾病與苦痛中掙扎成長。在這種無可改變的「現實」中,旁人對H夫妻決定的質疑其實反映了大多數人對於殘疾者生命的普遍看法。
主流價值對於殘疾兒最明顯的拒絕之一就是預防醫學所極力防堵的生下不正常孩子的機會。一但殘疾者出生,社會的修補機制也大多朝著使之「正常化」的方向努力,包括將之置於社會救濟的脈絡或是教育的脈絡,目的在於提供殘疾者存活技藝,使之有能力進入社會生產與勞力交換的機制,成為「有用」的人。在美國始於1970年代的殘障權利運動(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挑戰將「殘缺」(deficient)視為「無用」(invalidity)的觀點,認為殘障者失能的原因不在於生理或心智功能的缺陷,而是來自於社會的歧視與偏見。殘障權利運動的提倡者認為殘障既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醫療議題;對殘障的思考應該將之置於公民權利脈絡下來討論。無論社會對於殘障者的歧視或是慈善救濟的眼光都是運動者想要挑戰的視角。這個運動採取同性戀者權利運動(Gay Rights Movement)中「以差異為傲」(‘pride’ in difference)以及「出櫃」(‘coming out’)的理念與實踐,認為這才能使得殘疾者重新獲得真正的自主性與能動性(agency)。(Paterson & Hughes, 2000; Fleischer& Zames, 2001)。殘疾者不是「失能者」,而應被稱為「異能者」。殘障權利運動挑戰主流社會對於「正常」的定義,以及將殘障置於醫療論述或社會救濟的慣性思維,有很重要的意義。然而,爲許多殘疾兒的照顧者而言,並不是肯定了殘疾者的「異能」就能夠消解生命重擔的實在性。關於殘疾者的存在,以及其親人與社會對於此存在的種種回應,其實牽涉到複雜的倫理處境,不只是拒斥、修補或是增能(empowering)等思維可以簡單涵括。
對於殘疾者存在意義的反思,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 1935~2023)對於「殘疾」的書寫可以提供我們更進一步的思考。大江健三郎出生於日本四國愛媛縣,在東京大學法文系就讀時即以《飼養》一文獲得芥川獎,成為日本文壇極受矚目的學生作家。大江早年的小說具有強烈存在主義色彩,28那ㄧ年長子大江光(Hikari Oe,1963-)的出生爲大江帶來生命重要的轉折。大江光一出生即有頭蓋骨先天缺損,腦組織外溢的問題。雖然因為手術免於夭折,卻留下智力障礙的後遺症。如何與殘疾兒共生,因此成了大江生命中最重要的課題。在大江光出生的那一年,大江還去廣島參與了原子彈爆炸的相關調查,訪問了許多爆炸的倖存者,以及參與醫治工作的醫療人員。殘疾兒所面臨的死亡的威脅以及原爆倖存者在死亡關口的掙扎給大江帶來巨大的震撼,對於殘疾與死亡之課題的思索於是成為大江日後創作中重要的主題。1964年出版的《個人的體驗》的故事主人翁即是一位面臨殘疾兒出生之父親。除了小說中經常出現的殘疾兒角色,大江也以散文的方式書寫自己家庭與大江光共生的經驗,例如《療癒的家庭(A Healing Family)》與《寬鬆的紐帶》。大江光在五歲之前無法和人以語言溝通,大江夫妻卻意外地發現他對鳥鳴聲有特別的反應。大江光開始唸福利學校後,大江夫妻進一步發現他對音樂的強烈興趣以及敏銳知覺,於是大江光也開始學習作曲。雖然沒有常人的智力,音樂成了他與外界溝通的重要媒介。目前大江光已經出版了數張音樂專輯,他的專輯也獲得不少音樂的獎項。
從存在的裂隙到神聖的開顯
大江健三郎在小說《個人的體驗》中描述一位父親目睹自己親生之殘疾兒出生的情形:
就在這一瞬間,鳥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一個很難看的嬰兒,赤紅的小臉上滿是皺紋,眼睛像貝殼接口的縫,硬硬地闔著,鼻孔插著橡膠管兒,而閃著珍珠光澤的桃紅色的小嘴,則發著無聲的呼喊。鳥不禁抬起屁股,探著頭,他看到了孩子包著繃帶的頭。繃帶後面,血漬點點的脫脂棉里埋著的,很明顯,是一個異形的存在。 鳥幾乎不敢正視,轉臉坐下,臉貼在車窗窗框,望著匆匆向身後退去的街市。警笛驚嚇著路上的行人,行人們和鳥剛才看到的那群孕婦一樣,懷著好奇和莫名其妙的期待,注視著急救車。像突然定格的電影畫面,他們的動作突然不自然地靜止。這正是他們看到平淡的日常生活細微的裂紋的時刻。(大江健三郎,《個人的體驗》,斜體字為我所加)
這個因為殘疾兒誕生所遭遇的存在的裂紋,是現代優生學科技所要盡力防範的處境。也因為如此,當我的朋友H夫妻決定生下有缺陷的孩子時,會遭到許多質疑的眼光。醫學的技術原為減輕人面對生病的痛苦,以及幫助病人重獲健康、正常的狀態,這是一種對於「失常」的修補。預防醫學則更是要在疾病與失常發生「之前」,或者說,在其暗影拂照的當下斬斷其現身的可能性。當「不正常」被列入優生醫學企圖辨認並「處置」的暗影時,很容易落入ㄧ種對於追求「正常」的不假思索。這時候,優生學科技就成了海德格所謂技術世界之「座架」之一環:
我們身處語言之中,受到該歷史時代所設置之架座(Ge-stell)之擺置與逼索,朝向『被允許進入的歸屬之處』跳躍,與此座架同一,並以歸屬此架座為存在的依據,進而依此進行『對於一切的規劃與計算』。主體在語言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位置,認同的座標,而此位置與座標,是在他所處的時代中已經被設定或是正在形成中的架構。每個時代都在自行完成一個屬於該時代的架座,是個隱蔽而不須檢驗的立場,但是這個架構卻遮蔽了主體存有的整體狀態,這種遮蔽,是歷史的遮蔽,是遺忘。(劉紀蕙,2003:xvi)
宛若「異形的存在」的新生兒的誕生是優生學科技重重防護與遮蔽之下的漏洞與意外。殘疾兒因為其殘缺以及與死亡為鄰的狀態爲其照顧者開啟了存在的裂紋,也成為將照顧者由其日常生活的軌道拔出,拋擲到一個由照顧重擔所形成的深淵之中。殘疾兒的誕生打開了ㄧ道存在的缺口,這是技術世界計算性規畫的破裂與綻開。然而,就在這露出的豁口之中,原先對於主體存有的遮蔽也得以敞開。爲那與缺口直面的大江而言,這是他一生所面臨的重大危機。大江在《廣島札記(Hiroshima Notes)》於1995年所發行的英文版介紹中表示:「在我個人的生活中,面臨一個真實的危機,我的長子,ㄧ個男孩,出生時腦部有非常嚴重的殘缺,需要進行手術以挽救生命。有ㄧ位和我年紀相仿的年輕醫生警告我說,即使動了手術,他仍會是大腦殘障,人生將極為艱難。所以,我的生命真的遇到了一個僵局。」(Oe 1995:7)英文危機(crisis)一辭由希臘文演變而來,意味著選擇與「判斷(judgment)」的關鍵時刻。關鍵時刻也是主體被「逮捕(arresting)」的時刻,主體從日常生活慣習的重複之中被擲入存在的不安穩之中。這個不安穩的險境是生活的裂隙,從裂隙之中逼出ㄧ股力量,要主體從日常生活之中轉向,轉而關注存在的基本問題(Smith, 1992: 241-43)。大江說﹕「殘疾兒的出生,面臨情感極大的壓力,若不將自己推到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中,自己會因孩子的問題完全垮下來」。在這段黑暗的時刻中,廣島之行為大江打開人生的新視野。
在面對殘疾兒出生的困境的那一段時間,大江受邀到廣島參與禁止原子彈的世界大會。這個旅途意外地為他的困境投下一絲光芒。從1963年到1965年大江數次拜訪廣島,停留在廣島的期間,大江接觸了許多原爆的受難者,以及自身亦為受難者的醫生們。大江訪問他們對於廣島原爆事件的記憶、省思,並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寫下了《廣島札記》一書。受到原爆傷害、面臨病痛與死亡威脅的受難者與大江躺在醫院的初生嬰孩面臨著類似的處境。大江說:
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直接地給了我勇氣;反過來,我也品嚐到了因兒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種子和頹廢之根,被從深處剜了出來的痛楚。而且,我開始希望以廣島和真正的廣島人爲锉刀,來檢驗我自己內心的硬度。…我希望把自己理應具有的獨特的感覺、道德觀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單一的廣島這把锉刀上,通過廣島這個透鏡去重新加以檢驗。(大江健三郎,2002: 18)
在大江的眼中,廣島人在其苦難中所展現的是人在極限狀態中「幾乎絕望的勇敢」。(同上,頁35)因為承受輻射線的傷害而終其一生活在病痛與死亡陰影中的人們所展現的勇氣不是對抗死亡、朝向新生的搏鬥,而是面對悲慘死亡的搏鬥,朝向死亡的搏鬥。(同上,頁38)為大江來說,廣島人所經受的苦難使得他們成為「道德家」,無論那是展現在自殺者出於無奈而崩潰的道德,或是未自殺者在廢墟之中生存下去的道德。(同上,頁55、63)大江由於見證了廣島受難者無可言說的痛苦,以及醫生儘管在黑暗中摸索,卻不放棄的立場,得到一種力量,決定盡力讓孩子殘缺的生命延續下去。拜訪廣島的一個星期帶來大江生命的徹底轉變,大江自己稱之為「在廣島ㄧ週之後的皈依(One-week Hiroshima conversion)」:
在廣島的一個星期後,我對我個人生活的態度徹底轉變。廣島的經驗也徹底改變我的文學創作。在短短一個星期之內,我的生命發生了決定性的翻轉,避開宗教上的指涉,我將這個經驗稱為皈依。在三十二年後的今天,我甚至比當時對這個決定性的轉變有更深、更確定的覺知。…有些評論者說,我以廣島的現實做為飛越個人生活的反思的跳板,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是沒有錯的。(Oë, 1995: 7-8,,筆者自譯)
大江也曾說,這是一個「聖顯(Epiphany)」的體驗。Epiphany一詞有神靈之顯現與啟示之意義。大江不是教徒,但用了一個具有宗教意味的詞來說明這個經驗的性質。若將神靈理解為更具宗教根本性質之「神聖」(Soderblom, 1959),聖顯也就具有Eliade所言之「聖顯( hierophany)」的意涵。聖顯一詞是由希臘文「神聖(hiero)」與「顯現(phainein)」兩個字根組合而成,也就是神聖的顯現。以Eliade的話來說,
神聖對宗教人的意義並非單指對於上帝或諸神信仰,而是意識到生命的來源、力量、或是生命的實在(reality),存有者(being),意義,真理相關的概念。…體驗到神聖,意味著讓人超越渾沌脫序、危險事物或無意義的變動,找到生命的定向。(王鏡玲,2000: 34)
Eliade把神聖的體驗理解為生命由渾沌到定向(orientation)的過程。然而,這個過程是在日常生活的裂隙之中才得以開展:「神聖顯現在凡俗世界的對象時,在凡俗世界中形成一個裂隙(break),形成一個中心「定向」或「導向性」(orientation)」(Eliade, 1958: 459, 引自王鏡玲,2000:38)。這個凡俗世界的裂隙或缺口開啟了主體與神聖的聯繫,但這樣的開啟在初始為主體而言卻呈現為一種墮入黑暗中的經驗。如果用奧托(Rudolf Otto)的話來說,這由裂隙所開啟的「黑暗、靜默與空無」,恰是那作為「全然相異者(wholly other)」的奧秘(numinous)得以出現的條件(Otto, 1950:68)。猶如Denzin(1989/2000)將主顯節體驗理解為個人生命中難以抹滅的時刻或是危機時刻,有可能徹底扭轉個人的生命。這個生命的關鍵時刻是一個與全然相異者遭逢的經驗。此全然相異者不是理性辨察理解(canny)的對象,而是超越理性的奧秘,奧托稱之為「奧秘(numinous)」:「無論在何處,無論以什麼形象與我們遭遇,這個絕對相異者都是作為不可理喻、異常的,含糊的東西而出現的。」
為Eliade來說,從渾沌到定向的聖顯總是以象徵為中介。換言之,由遮蔽到開顯是一個以象徵為中介的過程。象徵一詞的字源學意涵原非名詞,而是動詞,意指將碎裂成兩半的錢幣同時「拋擲(sym-ballein)」的行動,以預示其即將來臨的結合。象徵事件(symbolic event)也就是兩個碎片(fragment)相遇與結合的過程。當其中任何一個碎片尚未遇到另一個碎片時,其意義仍然在黑暗中隱默著;換言之,在碎片結合之前首先是意義的斷裂與隱退。
象徵事件因此總是意味著一次遭逢,或者甚至我們可以說是存在於某個已被揭露的在場(presence)以及認出其(在場)的特殊目擊(witness)之間的一個象徵(sym-ballic)關係。(神聖的)在場以及(人類的)目擊在一個真實的見證關係(relation of testimony)中產生關聯,清楚地構成此遭逢的標記。藉著這個見證關係那被顯明的獲得了它的形貌。那被象徵的形貌宛若神的顯靈(theophany)、榮耀的靈光、或是明亮之光。(Trías, 1998: 105)
大江因為殘疾兒的出生,歷經生命最大的危機,卻也從廣島原子彈受難者的身上滋生出對於殘疾兒全新的理解,以及相應之倫理承擔。為大江的聖顯經驗來說,廣島原爆倖存者與殘疾兒就像是那被拋起的兩個碎片,在相遇之中彰顯了原先隱蔽在黑暗中的意義。殘疾兒的殘缺以及終生無法完全復原的狀態沒有帶來初生生命予人的盼望,反而將大江拋入絕望的極限狀態之中;廣島人在絕境中的領悟與勇氣:「天地盡,萬物絕,心傷始得慰」[1]卻讓大江看到從幾乎絕望中才得以看見的盼望。這盼望不在於逆境的移除,而在於對於逆境的承擔。宗教心理學家Pruyser曾經區別願望(wish)與盼望(hope)的不同﹕前者有一個明確的內容與對象,後者較為含混不明。人類能夠真正盼望的,是那種非常寬廣與普遍的,例如救贖、自由、生命那樣的東西。然而,在擁有盼望之前,主體先要經歷被「逮捕」、為一種特殊之人類境況(human condition)所捕捉的經驗。(Pruyser, 1992: 276)Pryuser從現象的分析發現,從此種絕境中升起的盼望並不是對於即將發生之事的預測或是宣稱,換言之,盼望與正確與確定沒有關連,而是一種耐心與容受。願望有明確的對象,所以總是朝向張力釋放的方向運動,盼望則與等待有關。為盼望來說,現實不是固定或凝滯的,而是開放的。為懷抱盼望的人來說,現實總是存在著尚未被發掘的資源與可能性。(同上,頁278)
從奧秘的見證到應答
對大江來說,殘疾者的存在既是挑戰,也是召喚。這樣的思維與反省是對世俗價值很大的逆反。神聖的奧秘超越道德與理性,卻成為道德的基礎。對於奧秘的體驗賦予生活倫理一種使命(武金正, p. 46)。換言之,與不可理喻之全然相異者的遭逢帶來一個應答的責任,責任的應答是一種「飛躍的行動」,就如研究大江文學的評論者所說的:
連讓孩子接受手術的决斷,從一開始也不是那種對「正统」的求生方式的追求,它也只是一種突然的「身體深處」發生的變化。把這「深處」叫無意識也好,内部的真實也好,都是危險的。與其說成這樣,不如說成是連自己也搞不明白的一種飛躍的行動,它的不可知性在「身體深層」是種說不明白的什麼巨大的堅固的存在,它只是以這種樣子表現出來。(桑原丈和《大江健三郎論》,斜體字為我所加)
是否爲殘疾兒動手術的決定,是一個面對黑暗的經驗,也是與大江自己生活基本價值的一場對决。大江可以決定放棄手術,讓這個因為殘疾兒誕生的生命裂口彌封,或是做出向著黑暗縱身一躍的決定,投入裂口中,以求得見黑暗中的光明。大江將兒子取名為「光」,其實是在最深刻的黑暗中對於光明的渇見。這個面對黑暗的經驗亦可理解為「普遍責任」與「絕對責任」的對決。Derrida以亞伯拉罕獻子的事件展開他對「絕對責任」的思考。若責任意味著對他者的回應,那麼「絕對責任」就是那屬於倫理卻又超越倫理的責任:
…他者在倫理上的獨特性,並非一般倫理學意義下那種有賴普遍道德規範之應用的個別處境,而是一種全然獨特、不可取代、不可重複的單一處境。在此一處境中做出的判斷乃是一種瞬間的、被逼做出的決斷。這種瞬間決斷彷若一次跳躍。…與傳統的倫理學相較,這樣一種出於他者的召喚而做出的決斷至少有三重難關:沒有足夠的時間、沒有足夠的知識、沒有足夠的先例。面對不可決定性的深淵(the abyss of indecidability),任何決斷都像是一次無法預知結果的跳躍。而也正是這樣一道不可決定性的深淵,讓一種全然慷慨的贈與得以可能。(鄧元尉,2003:154-155,斜體字為筆者所加)
大江在小說與散文中都表達過這種「普遍責任」與「絕對責任」的張力:「養育著殘疾的孩子,你這是要幹什麼!把這個殘疾的孩子置於家庭的中心,你這是要幹什麼!與其把力氣放在對社會更有用的改革之上,把精力放在無用的殘疾兒之上,你這是要幹什麼!」(大江健三郎,2004:72-79)全然慷慷的贈與飛躍過計算衡量的經濟學,以不可理喻的決斷面對難關。然而,這種慷慷的贈與不能被理解為被主體肯認的英雄式救贖行動。為大江而言,與其說他們承擔了殘疾者的殘缺,不如說殘疾者的殘缺構成他們被「轉送到另一種狀態」的視角,這個視角揭露了他們真正的歸屬之地(Gargani, 1998: 119)。大江曾說,自己是通過和這個孩子共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為小說家的生存方式:
我把寫作這些小說期間日本和世界的現實性課题,作為具體落到一個以殘疾兒童為中心的日本知識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來理解和把握,持續不斷地把這樣的理解寫成隨筆。我認為,殘疾孩子的誕生和與其共生這樣一個偶然事件,和對此的有意識的接受,在那以後,經過了37年,到現在,塑造了我作為一個小說家的現實。…通過布萊克、葉芝,特别是但丁——通過對他們的實質性引用——我把由於和殘疾兒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帶來的神秘性的或者說是靈的體驗普遍化了。(斜體字為筆者所加)
為大江而言,這些「靈的體驗」是透過與大江光的日常相處以及大江光所創作的音樂而理解到的生命的黑暗、無可抗拒的慾望與飛躍的衝動,以及被禁錮的靈魂巨大沉重的悲傷;但同時也是喜悅與活力。大江在關於家庭日常生活的隨筆中曾經紀錄了大江光與家人之間異樣的溝通:
了一個以布萊克的詩為基調的中篇《爸爸,你要去哪裡?》」從下面的這段對話中,我開始在小說裡把兒子的名字叫做義么。
飛吹著他那因吃熱湯麵而漲紅了的臉,我蹬著自行車回家,反覆問他:
——義么,熱湯麵和百事可樂好吃嗎?
——義么,熱湯麵和百事可樂好吃。
兒子這麼一答,我就為感到現在我們父子之間已經達到充分的溝通而滿足。(Oe, 2002)
昨天吃過飯後,光的母親和光的妹妹坐在桌旁好像在聊年輕的女性如何自立的問題。女兒說,獨立生活,就需要公寓的一間房子。而房子實在太貴。自己以前在大學圖書館的工資大部分都存起來了,但是這些錢都買不了哪怕是報紙廣告上宣傳的廉價公寓。…女兒根據社會的現實情況流露出新中的鬱悶。…這時,光走到掛在大門旁的紙箱前—紙箱裡放有一些硬幣,都時出門買東西找回的零錢,順手扔進紙箱裡,以作為支付各種費用時的零錢—把裡面五十日圓和一百日圓的硬幣全部拿出來,放到妹妹面前的桌子上,彬彬有禮地問道:『這些夠嗎?』(同上,pp.78-79)
傷口與共生
大江曾在《廣島札記》中提到,廣島就像烙印在全人類之上一個赤裸的傷口,如同所有的傷口,不是走向人性復原的希望,就是走向徹底毀滅的險境。(Oë, 1995: 97-98)傷口所開啟的裂隙揭露了「人類正在參與的真實存在處境」(王鏡玲,2000:41),與此處境直面的大江才能做出以自己的餘生與殘疾兒共生的決定。「共生」意味著與受難者或殘缺者「同在」,用大江自己的話來說:
就我們而言,除了做為「受害者的同志」,我們已無法做一正常的人。…他們真正體現著廣島的思想,決不絕望,也不奢望,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忍不拔。我把這些人看做是原爆後最正統的日本人,我願與他們融為一體。(大江健三郎,2002: 134)
就我們而言,除了做為「受害者的同志」,我們已無法做一正常的人。…他們真正體現著廣島的思想,決不絕望,也不奢望,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忍不拔。我把這些人看做是原爆後最正統的日本人,我願與他們融為一體。(大江健三郎,2002: 134)
大江決定盡力挽救殘疾兒的決定是逆反社會主流價值的決定,但這些決定的逆反性質與殘障權利運動「殘而不廢」之論述對於「殘即廢」之認定的抵抗存在著微妙的差異。如同殘障權利運動一樣,大江不貼著「醫療」、「啟智」、「教養」、「教育」、「培養獨立技能」、「走入社區」的思維作為認識殘者處境的基礎。大江全家人(包括大江、妻子、暨大江光之後所出生的一女一兒)以大江光為中心所建立起來的、以「寬舒的紐帶」維繫著彼此的家庭,也與權利運動所強調之殘疾者的自主與自尊有所不同。大江透過與殘疾者共生的經驗而所達到的洞見(insight)是一種神祕的體驗,或者稱之為對於奧秘的瞥見。這樣的奧秘並不驅除殘缺,反而藉著接近殘缺、穿過殘缺的黑暗而帶領自己翻轉到自己的反面。這樣的翻轉既是離開,也是回歸。Vattimo對於宗教經驗的理解可以作為本文暫時的一個結語:
人們常說宗教經驗是一個離開(leave-taking)的經驗。然而,假如這是真的,那麼這個展開的旅程很可能就是一種回歸。在宗教中,某些被我們認為不復記憶的東西重新現身,某個蟄伏的痕跡重新被喚醒,某個傷口重新被開啟,被壓抑的重新回返,我們過去所認為的克服(Ǘberwindung)…只不過是一種熬過(Verwindung),一個漫長的康復,此康復再一次與疾病難以消抹的蹤跡妥協。(Vattimo, 1998: 79)
後註:這是多年前一篇研討會文章的內容。大江健三郎於今年三月三日離世,我將當時的論文內容做一些調整,感念他對於我思考宗教研究與障礙研究的交會時,所提供的種種啟發。
參考文獻
大江健三郎,1995。《個人的體驗》,王中忱等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
–1995。《大江健三郎作品集》,葉渭渠主編,北京:光明日報出版。
–1996。《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葉渭渠主編,作家出版社。
–1996。Hiroshima notes.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2。《廣島.沖繩札記》,王新新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寬鬆的紐帶》,鄭民欽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王鏡玲,2000。《神聖的顯現:重構艾良德宗教學方法論》。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武金正,2003。〈啟示與醒悟的奧秘之道〉《輔仁宗教研究》,第七期,頁45-74。
劉紀蕙,2003。〈導讀:文化主體的賤斥〉,茱莉亞.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台北:桂冠出版。
Denzin, N.K, 張君玫(譯)。1989/2000。《解釋性互動論》(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台北:弘智文化公司。
Eliade, M. & Sullivan, L.E. 1987. “Hierophany.” In M. Eliade(ed.),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Methodological Remarks on the Study of Religion’s Symbolism.” Mircea Eliade and Joseph M. Kitagawa (eds.)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Essays in Methodology
Fleischer, D.Z. & Zames, F. 2001. 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From Charity to Confront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Gargani, Aldo. 1998. “Religious Experience as Event and Interpretation.” In Religion, edited by J. Derrida & G. Vattim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Oe, Kenzaburo. 2002. Rose Up O Young Man of the New Age. New York : grove Press.
Otto, R. 1950. The Idea of the Holy: an Inquiry into the Non-Rational Factor in the Idea of the Div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ational. Translated by J.W.Harv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中文版:魯道夫.奧托,《論神聖》,成窮、周邦實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Paterson, K. & Hughes, B. 2000. “Disabled bodies,” in The Body, Culture,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Pruyser, Paul W. 1992. “Phenomenology and Dynamics of Hoping.” In Experience of the Sacred: Reading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 Edited by S.B. Twiss & W.H.Conser, Jr. Hanover & London: Brow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John E. 1992. “The Experience of the Holy and the Idea of God.” In Experience of the Sacred: Reading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 Edited by S.B. Twiss & W.H.Conser, Jr. Hanover & London: Brown University Press.
Soderblom, N. 1959. “Religion.” In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edited by James Hasting., vol. IV. New York : Scribner’s.
Trías, E. 1998. “Thinking Religion: the Symbol and the Sacred.” In Religion, edited by J. Derrida & G. Vattim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attimo, G. 1998. “The Trace of the Trace.” In Religion, edited by J. Derrida & G. Vattim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 這是大江健三郎在《廣島札記》中所引述的一位受難者所寫的詩,參見第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