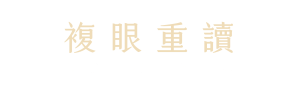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講者 | 藍劍虹(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演講時間 | 2024/04/14
責任編輯 | 吳寧馨
協力 | 黃奕偉
逐字稿整理 | 林沅錚

今天講題ppt標題圖片(圖1)是阿根廷巴塔哥尼亞史前洞穴,手洞 Cueva de las Manos(距今約1萬~9000年前)的圖片。使用這張圖片,主要是因為它描繪了手。這個史前洞穴之所以叫做「手洞」,正如此圖片上可以看到的,佈滿了很多手。今天的講題,正是圍繞著手這個圖像而展開。
那時收到宗教學系〈藝術、靈性與療癒〉課程的邀請,心裡其實頗有點猶豫,因為一來我個人沒有什麼宗教上體驗。二來個人基本上是一個啟蒙運動的立場。後來,對宗教的想法的改變,主要是兩點。第一,發現幾乎任何有人類的地方,不管是多小的部落、族群都會有宗教信仰。這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是需要嚴肅加以面對的。第二,比較個人因素的部分,就是因為探尋藝術、文學、神話敘事的起源,才開始將這個探尋與宗教聯繫在一起,也開始了解到,文學、藝術與宗教有其共同的起源性的連接。不過,也應該補充,這裏應當沒有涉及,可能是宗教最為核心的「信仰」部分,而比較是涉及到兩者的起源性的機制。就是想像力。
也因此想到那就從藝術體驗的角度來切入。希望一方面可以說明藝術這個也是人類自從亙古以來就有的行為現象。另一方面也能去處理宗教起源的問題。所以這次會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談藝術體驗。這會從我個人體驗開始,切入到繪畫的身體,和其中的關鍵點:觸覺和手。這部分對「手」的論述,也是對當前數位時代的一種回應。第二部分,則是從藝術和文學的角度切入來看宗教。從想像力的機制和敘事機制的角度,後者則主要借用人類學的「瑪納」(Mana)概念來處理。最後會透過「手」的意象,結合前述兩部分,提出兩種手和兩種神的想法為結,這是對當前時代的一點反思。
美術原來只是我的脫逃出路
—畫畫是把答案放在你前面,抄多少算你的
—把答案抄得不像的時候,老師反而會說你很有創意
—藝術比較沒有規劃這種東西,它就必須站在當下感受去進行
我先從我個人的繪畫經歷開始——會這麼做,不是因為得跟各位介紹一下自己,而是心裡有點仿效某種「宗教修行」體驗吧——回顧地來說,美術對我來說是一個脫逃的出路。因為以前非常不喜歡學校,每個方面都覺得不好(喜歡看書和台灣學校教育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後來就去唸美術班。記得那時是去長榮中學讀書,開學第一天朝會時,知道學校有成立美術班。進了教室還沒有坐定就跟導師說要轉過去唸。導師說,家長同意就可以。回家後詢問,家裡不同意。我堅持,並說若不給我念,那我要離家出走了,這才讓我去。回想,那是第一次為自己做決定,也是一種叛離世俗的開端,直到今日。
唸美術班,我先講件比較有趣的事:以前考試,內容都寫在課本上面,可是不讓你抄。那畫畫就不一樣了,畫畫是把答案(靜物、石膏像等)放在你前面,抄多少算你的。更有趣的事是,你故意把答案抄得不像的時候,老師會說你很有創意。念美術班三年期間,對我影響非常大,尤其是繪畫訓練的過程,給出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日。
剛開始學畫的時候,其實蠻挫折的,因為以前都沒有學過,只是自己喜歡亂畫。一開始就會看老師示範和同學怎麼畫、試著照著方法去畫。我很認真學,可是每次總畫不好,成績也都不理想。到了高二下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天下午在畫水彩靜物,畫到一半過後,我看著那張畫,覺得完蛋了。心想努力一年多還毫無起色,心裏有點絕望。接著,既然已經絕望了,畫也沒有救了,心想就不管它,亂畫吧。接著就隨性畫,畫著畫著竟還挺投入的。畫完時要交出去時,我還記得那時刻:看著那畫,心裡想著說,這張畫應該成績很爛吧;可是沒有想到,成績竟然挺好的。我本來以為老師是用電風扇亂吹,才給我比較好的成積,可是後來發現不是耶,我自己隨性畫反而成績都比較好,也比較有感覺。後來高三下的時候,有次老師跟我們講,畫畫跟其他事情不一樣,其他事情會按部就班的來,能夠預期怎麼樣,再按部就班去畫;可是畫畫不是如此,而是每一次下筆時,感受是對的,如此運作下來,那最後畫就會是好的。
我想藉此指出的,這當下感受的重要性。這也和其他學科的講究規劃或是按部就班的訓練不同。我想,藝術必須站在當下感受去進行。但是,這裡也需要補充說明,這裡的「隨性」,不是一般日常上的隨意,是指要能相當具體地跟隨感受去運作。
還有,繪畫也並非沒有「規劃、計算」,只是那不是,比如說蓋房子的那種規劃或計算,它還是需要去考量種種,比如背景要先畫,水分濃淡乾濕的掌握等等,其實相當複雜,但是這種規劃考量,是得跟隨感受去運作、掌握,沒有預先的藍圖,但是有個類似心象的東西,要去掌握到,跟隨之,然後這是身體與物質材料之間的應對交纏,身體和手,在其當下,跟隨其發展中的流動——可以試著想想看,比如一張水墨山水畫,其間有山石,有松樹和繁多的松針,和其他林樹等等,可是整張畫都沒有打什麼細密的草稿,而是必須每一筆落筆都得是對的,中間自然不可能有什麼修改,直到整張畫完成——那是一種身體、手,其自身的思維運作。
這不容易言說,因為是屬於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領域。在如此進入身體、手和媒介的遭逢的體驗後,在高三畢業前,我想,我跨越了進入繪畫這個領域的門檻,成績也變好了,隨後,聯考的術科考試,也獲得很好的成績,順利進入美術系就讀。比較意想不到的是,這三年和隨後的幾年繪畫生活所形成的種種,如今回想起來,影響竟是持續至今,我想,是我個人生命經驗的核心部分。
藝術是建立在物質上的精神性
—必須要整個身體投入,才能進到一筆一畫中。
—美術教育的「感受」,以榴槤作「感受」的現象學還原。
—戲劇表演可以把日常以為的「真實性」瓦解,從價值判斷「還原」到感受,我認為所有的藝術都是有關於感官的教育
關於物質/材料。藝術當然是精神性的,可是這個精神性是建立在物質和材料之上的,這也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跟繪畫打交道的經驗要有顏料、顏色調配、水分的控制、不同的紙張畫筆⋯⋯。在繪畫中,身體是與這些物質打交道。我從自己最初體認的一個很基礎的經驗來說明。那時候考美術系也要考水墨,上國畫課老師講解完東西方繪畫的差異時候,他派了一份作業:要交二十張畫,前面十張是要在宣紙上面畫直線,另外十張畫橫線。我想,哪有那麼簡單的作業啊。就拿著毛筆在宣紙上畫直線和橫線,試著畫直一點就是了,畫很快、不到一小時就畫完。可是,交出去後全部都被退回來了,沒有一張是及格的,不是因為畫得不夠直。後來老師邊示範邊講解,橫線必須要使用中鋒(毛筆)、以全身的力氣去畫。之後,你會發現你必須要整個身體投入才能進到一筆一畫中。
物質媒材的英文medium這個詞,其實是跟「通靈」有關的——這點後續會提到——整體而言,美術教育是以「感受」作為最基本的事物建立起來的。不過,「感受」這個詞,可能大家常有誤會。比如說,你吃了一碗麵或一個蛋糕,你覺得好吃。你覺得這是一種感受的表達嗎?很多人會覺得這是感受表達,不過,不是。它其實是很明顯一種價值的判斷。
那什麼是感受呢?我用現象學還原舉個例子,不過是用我自己的理解,例如:榴蓮,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是臭的,可是也有很多人喜歡榴蓮,覺得很香。之前我們所上有馬來西亞的同學就很喜歡吃。不過,當我問她在喜不喜歡吃台灣臭豆腐時,她卻表示,無法接受,並說那臭得不得了。
香和臭已經很接近感受了,但還不是感受。感受必須回到味道自身,在那裡是沒有所謂「香」和「臭」的,它就只是味道自身。要自己去接觸榴槤親自去感受。很多年前,當台灣開始引入榴蓮之後,我就試著去進行榴槤感受的還原。
我首先發現那是一個食物高度熟成的狀態,就像廚餘或其他水果的過熟,或者類似垃圾的發酸發臭。這真的是臭嗎?我那時想到,狗會在垃圾堆找這些東西吃。我就轉換想像我是一隻流浪狗,而榴蓮就慢慢地轉換成一種香味出來。透過這樣的設想,我喜歡上吃榴蓮,也覺得榴槤很香。後來,好一陣子沒吃之後(因為周圍的人會覺得臭),有次在市場再次碰到榴槤時,我心想:那現在它還是香的或是會變成臭的?靠近時,我去聞著,然後,在某個持續的短時間內,很好玩的,我發現到,這時候的榴蓮既不香也不臭,它就是它自身的味道本身。這是蠻有趣回到感受自身的例子。
那大家可以想想這樣的轉換——在心理學中這被稱之為「認知改變」,是可以應用在生活中的。比如說我們常對某個人、小孩、同學會貼上標籤或刻板印象,所以能進行這種還原,把這些印象、標籤等等懸置起來,回到此人的本身。我覺得這是相當重要的事情,對教育來說。另外,在文學上,那其實也就是所謂的「回到文本」。
個人的另一個藝術方面的體驗是戲劇,尤其是關於表演。戲劇表演課有很重要的training(訓練)是男生要扮成女生。最早也是在高中時,一次類似聖誕晚會之類的,我就穿著胸罩和洋裝、高跟鞋,還有假髮,演個老太太。那時當成遊戲玩,不過效果蠻好的,不知情的同學還以為是同學的奶奶來了。這樣的訓練有助於打破我們自身的認同,也打破穿越對男性和女性的刻板認知。大家可以試試看:你如果是男生,回家找女生的衣服穿,試試看戴個胸罩、裙子去體會那是什麼情況?我們對何謂男性和女性的概念就這樣被「扮演」整個還原回去了。
這個時候,對什麼是人,這件事情,會有不同的想法。在表演中,可以touch到各式各樣人的種種現象和感受。再比如說,你認為你是一個個性暴躁的人,卻演一個拘謹的人,或是你認為你是一個敏捷的人,要演一個行動遲緩的人。在這樣嘗試的「扮演」後,你原有的行為模式都會被還原回去,我所說的還原是指,不再具有「真實性」。「真實性」,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東西是香的還是臭的,榴槤那麼臭的「真實性」會被瓦解掉。我想這種扮演的教育是很重要的。比如性平教育。一位陽剛會嘲笑陰柔男性的孩子,在成功扮演女性角色,比如白雪公主好了。那之後他再也不會嘲笑別人「娘」了,因為他曾經比誰都還「娘」呢。而他也會得到他以往身為陽剛男性之外的體驗與感受。如果概要地談,我覺得所有的藝術都是有關於感官的教育。
「打架」的繪畫作品與戲劇系經驗
—帶著一支筆去看,和只用眼睛看東西,是很不一樣的狀態
—畫畫是直接肉身相搏的東西,不過打架的對象是和材料紙張相互交纏

這邊給大家看我後來的作品,圖2是在台東大任教後,有次在杉林溪畫的,另一張是在馬太鞍濕地。(圖3)在台東鹿野和安平畫的,是鉛筆和蠟筆畫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畫畫的經驗,事實上鉛筆和蠟筆很不容易做到這樣的效果,那是跟蠟筆進行某種抗爭後畫出來的。一般我們拿鉛筆、蠟筆時,是直著握筆。不過這些畫不是這樣執筆的,而是橫著拿的。這方式是這樣發現的。就是覺得直式握筆方式不對勁,不稱手,無法表達,總是覺得有所阻礙。在一番我不知道該如何描述的操作狀況後,我打破了那種慣常執筆的方式,粗暴地將它們以橫、斜的方式來操作,最後發展更熟練的橫向執筆的技術。回顧起來,應該可以這麼說,我察覺慣常執筆的畫法,會讓這些媒材侷限在點與線的表達內,而我不滿的地方就是在此。而以橫、斜的方式,則可以讓這些媒材突破點、線的表現限制,拓展到面的呈現,從而給出既有線也有面的交織表達可能。

另一張是在宜蘭明池畫的(圖4),媒材是水彩。其實我個人不喜歡旅行,因為旅行都太短,一天到三、四個地方時間太短實在不喜歡。去明池的時候,我在這裡就待了四天,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池子,在那待了四天這種旅行我才會比較喜歡,那這種旅行帶著一支筆去畫,通常會讓你更進入環境當中,帶著畫筆看景物,和只用眼睛看是很不一樣的狀態。這是在貓鼻頭畫的(圖5),那時候是在一個懸崖上畫的,頂著大太陽畫了約有一兩個小時吧。這是在高雄西子灣畫的(圖6),那時我在中山大學兼課,帶學生去畫,看起來很像鉛筆不過實際上也是蠟筆畫的。這個做法,就像前述的方式,是橫著運用蠟筆的方式畫的。



另外這畫,大家可能不熟悉,這是在屏東的牡丹,那裡有個哭泣湖(圖7)的地方。那時要動手畫之前,面臨一種無法下筆的狀態。景很吸引我,可是不知道該怎麼畫。所以,約略是對眼前的景,看了兩個小時多才下筆畫的。下筆時,其實也不知道該怎麼畫。這裡,有個東西得說一下。就是,腦袋不知道怎麼畫,可是看了兩個小時多,突然感覺可以畫,但是,那時候其實不是理智上覺得可以畫了,而是雙手自己拿著筆畫了起來。

手,會跑在心智之前。手和身體自己會知道怎麼去做。我覺得我是跟隨在手、畫筆和紙上的種種之後的狀態。我覺得這很像「打架」。我教畫畫的時候喜歡使用「打架」這個詞,我不知道大家現在有沒有什麼打架的經驗?我倒覺得打架是種重要的活動(雖然現在大家都禁止打架)。因為,打架不是像電影武俠片一樣套好招的,而是直接肉身相搏的東西,身體在和另一個身體的直接當下去互動,而且是某種生命交關的壓力下進行。在畫畫時,打架的對象不是某某人,而是我們的身體(手)和材料、紙張相互交纏搏鬥。
兒童美術教育
—唯一的一條規定就是不准使用橡皮擦,為了要在當下承接那即將到來的東西
—我覺得真正的原住民應該是小孩吧?
—人只要會說謊就代表他有虛構的能力……
回國之後,我主要的工作是教兒童美術,一共教了大約二十五年,剛好在疫情前一個月我決定停止教學活動。我們教室唯一的一條規定就是不准使用橡皮擦,當然也是不打草稿、直接落筆的,為了要在當下承接那即將到來的東西。這點是我非常重視的部分。不使用橡皮擦,原因就像前述,排除預期規劃,直接面向繪畫啟動的生成時間。這和我們平常的時間概念不同。那不是鐘錶的時間(鐘錶其實給出的是hours,而不是time),而是某種接近「時機」或是某種事件發生的時間維度。
美術教育的經驗後來集結出版,共有三本:《以塗鴉對抗填鴨》是關於繪畫觀念,《塗鴉畫冊,放牧的眼睛》談的則是繪畫課程。這兩本是由人本教育基金會出版,出版前是在人本的月刊上連載。[1]最後一本是《許多孩子許多月亮》,則是關於教室裡那些在畫畫的孩子,由晴天出版社出版[2],後來也有簡體版。[3]因為這些書就和兒童文學研究所(臺東大學)有所聯繫,之後跑去唸博士班。念完後任教也做了所上學刊編務,後來還出版《可不可以畫》的繪本[4](那本書是在博士班的時候畫的,到去年才出版)。
民國一百年承接《獵托邦傳奇》[5](圖9),用插畫說原住民狩獵的故事,圖10右邊用原始洞穴的概念,左邊就是原住民捕獵的狀況,這是儀式和森林受到危害的場景(圖11),圖12、13也是模仿原始洞穴,上面是我教室小朋友的畫,因為談到原住民的時候,我覺得真正的原住民應該是小孩吧?這一張(圖14)有引用了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做的雕刻,那是一輛摩托車。我覺很有趣的地方是,輪子的部分是百步蛇捲起來形成的。後來就把這圖像放到學刊上,那一期是關於「原住民兒童文學」專題,封面是我負責設計。那時設計的學刊封面上都會有個小木偶人。其行走的姿態構想是來自於Giacometti的「行走的人」,這照片拍攝的人是布列松;小木偶自然是來自《木偶奇遇記》,我很喜歡Pinocchio因為他會說謊,人只要會說謊就代表他有虛構的能力(這點後續會提到)。






我的繪本《可不可以畫》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靈感來自香港女作家西西的詩,這首詩叫〈可不可以說〉:
可不可以說
一枚白菜
一塊雞蛋
一隻青蔥
一個胡椒粉?
可不可以說
一架飛鳥
一管椰子樹
一頂太陽
一巴斗驟雨
可不可以說?
一株檸檬茶
一雙大力水手
一頓雪糕蘇打
一畝阿華田
可不可以說?
一朵雨傘
一束雪花
一瓶銀河
一葫蘆宇宙
可不可以說
一位螞蟻
一名蟑螂
一家豬樓
一窩英雄?
可不可以說
一頭訓導主任
一隻七省巡桉
一匹將軍
一尾皇帝
可不可以說
龍眼吉祥
龍鬚糖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詩,我想如果這首詩能收入到國小課本,台灣文學教育就有救了。因為這樣我才會創作這本繪本,希望有天這首詩可以收到課本中。這繪本比較特別就是可以在裡面畫畫(圖15)。我自己也很喜歡在買來的繪本裡畫畫,所以我自己在畫完這本書的主要圖像後,也在上面添加東西。比如,這畫中有個迷宮,那本來以為可以從左邊進來、再從右下邊出去,結果畫完,發現竟是走不出來的(圖16)。既然走不通,那我就加個樓梯讓那隻小小豬可以跑出來。不過,最近我又重新走一次迷宮,發現這樣其實也走不到樓梯的地方。那書的基本想法是可以隨意組合的圖片構成(圖17),用這樣的遊戲性來對應西西的那首〈可不可以說〉(圖18)。




把身體借給世界,畫家才能把世界轉變為繪畫
—身體和手之所以能成為具身性技藝的基礎和掌握者,有賴於一種我們平常忽略的感官「觸覺」。
—具有想像力的觸摸,才能把物質中沉睡的性質召喚出來
—是觸摸這種雙向的交互,才能變成精神上的物質。
接下來想談身體和觸覺,從理論層面上做個說明。這裡引用梅洛龐蒂在《眼與心》[6]:「是透過把身體借給世界,畫家才能把世界轉變為繪畫」。事實上我們也真的看不出一個心靈如何作畫,意思是只有心靈或靈魂是沒辦法運作的。梅洛龐蒂說,身體和手之所以能成為具身性技藝的基礎和掌握者,有賴於一種我們平常忽略的感官「觸覺」。曾有人問過,如果只能保留一個感官的話,那我們要保留哪一種?我想很多人會回答說是視覺。然而,可能最重要的感官是觸覺。這裡可以想想觸覺的重要性何在?(試想,我們伸手卻摸不到眼前的東西,甚至無法觸摸到我們自己。)
皮膚科醫生萊曼(Monty Lyman)在《皮膚大解密》指出,皮膚這個器官是人身上最大的器官也是最迷人的,它也是我們心智上親近的朋友,其他器官的重要性都比不上皮膚。也是我們人類所知最少的器官。梅洛龐蒂晚期有提過一個概念,La chaire,這個詞通常翻譯為「肉身」。不過香港學者劉國英主張把它翻為「肌膚的存在」,我蠻同意的。萊曼說:「人邊緣的東西才是人的核心,人的皮膚就是我們自己」。法國詩人梵樂希則說:「人身上最深邃的地方就是皮膚。」而繪畫可以被視為「表面功夫」,而這種表面功夫卻是最深邃的。這裡我想到眼睛。我們會說一個人眼神很深邃,但是不管是從眼球本身,或是從眼睛到後腦勺,也不過十幾公分,為何會給出所謂深邃之感?這案例表明,表面是可以是給出深邃。我想,「畫面」這種表面一樣是如此。
梅洛龐蒂提出:「繪畫是透過操作著的身體,使自我能裸裎在世界中」,所以在跟自然交纏操作的時候,繪畫才會變成畫者肉身的展現,也就是我剛剛說的「打架」的運動的狀態。繪畫有它的身體和肉身,就跟身體皮膚一樣,它有一種質變,這個質變或也可以從宗教的角度來解釋了,就像耶穌基督轉變成葡萄酒和聖餅的質變過程,所以說梅洛龐蒂才說:「是透過把身體借給世界,畫家才能把世界轉變為繪畫。」這裏要談一下「圖畫的手勢」,也就是對畫家來說身體的運動是比任何觀察、想像和構圖都還要關鍵的,任何意義的到來勢必會依賴某種手勢的產生。
透過身體的運動具體打開一個世界,世界化身為肉身,我不知道基督宗教對「道成肉身」的解釋是什麼,但是我覺得這似乎能對身體的運作、畫面的轉化有所說明。這過程並不是畫家對媒材工具的控制,如果是控制,那就會變得像是數位技術的東西,因為媒材和物質是會對畫家的身體產生抵抗的,就像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說的「對反」(contre)。我們畫畫必須跟顏料互相依靠,在一個想像者的眼中,物質會顯現出一種抵抗並顯現在作品當中,而這抵抗就是我說的「打架」。我在教畫的時候常說得要去「打架」,但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些話的意義放在現象學中是相同的,因為在觸摸中手涉入了「對反」或「反抗」種種遭遇。
畫者是跟種種媒材的交會、交手,這邊要注意的是,不只是畫者跟媒材的觸碰而已,而是物質一樣反過來觸摸畫者的手。就如米開朗基羅在聖西斯汀大教堂的繪畫,那著名的上帝與亞當之間接觸手勢。這讓我想到,巴舍拉引用德國浪漫主義詩人諾瓦利斯(Novalis)的說法:「每次觸摸都孕育出一個實體,其效果與觸摸是一樣持久的。」實體觸摸著我們的行為,它堅硬或輕柔如同我們觸摸著它們一樣,這相互交纏喚醒了物質,也是這樣具有想像力的觸摸,才能把物質中沉睡的性質召喚出來。就像畫西斯汀教堂的米開朗基羅說:「觸摸賦予生命」,那是雙向的交互,因為這個交換才能變成精神上的物質。這也是為什麼傳統繪畫的媒材都需要數年的掌握,需要終身探索。
手的知性:亞歷山卓・桑納的戰爭之書
—亞歷山卓・桑納相當厲害水分的控制,或者應該說是:不控制,讓水分在媒材上流動,把偶然變成必然
—我始終信任在畫畫中的雙手,他們會找到最好的方式來描繪出某片天色、某座山和洶湧的海
—是意圖掌控一切的手把戰爭加上技術,變成大砲、原子彈……
—如盲人一樣畫圖,不費時間處理細節,而是尋找生命的脈動
接下來透過一個案例跟大家說明,我把這案例的小標題定為「手的知性」[7]。案例是義大利插畫家亞歷山卓・桑納(Alessandro Sanna)。他的《快樂之手》(Mano Felice)系列畫本,就希望大家能動手去畫,書封可以看到裡面的手在水、大地、火的狀況,還有盜火者所持的火把跟普羅米修斯是不一樣:火種其實就持在手本身。另外一本是講戰爭的書《如同此石》(圖19),我有寫篇導讀。[8]書裡面的石頭就是地球的比喻。我們先看他作畫的紀錄片(請參閱youtube影片)。我們可以看到他畫畫不打草稿的。他的《皮諾丘前傳》的畫也是不打草稿。在這影片,我們可能首先驚訝亞歷山卓・桑納相當厲害水分的控制,但是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到,他是擅於「不控制」,讓水分在媒材上流動,然後即時地在當下承接之,並把偶然變成必然。他的《長河》、《白鯨記》也都是這樣不打草稿,流暢地一個畫面接著一個畫面而形成的。

《如同此石:一切戰爭之書》是從遠古時期的戰爭一直講到他當時創作當下的敘利亞戰爭。他是義大利人,當時很多敘利亞難民逃到義大利,促使他畫這本書,全書一百六十頁完全沒有文字,全部沒有打草稿就這樣畫下來。這本書是桑納在思考從遠古以石互擊到現代的坦克、飛機和原子彈的戰爭問題。在此,我從這裡提出的核心問題是關於「技術」問題。
先看一下此書部分內容。他畫面分鏡非常好(圖20)。我這邊已經做擷取和編排。他有些畫面運用了影像,如這是載運猶太人到集中營的火車,長崎廣島戰後影像(圖21)。還有原子彈爆炸後景象,這裡我選的配音是原子彈試爆的聲音音檔。書中最後有幾年前的難民,現在我們觀看此書當下,則是有烏克蘭戰爭。書末,桑納把畫面鏡頭往太空上拉昇,讓我們可以看到位於宇宙中的地球(圖22)。這景象就如作者在〈後記〉中提到:「從遠方的星塵看來,一顆遠方藍色的明珠,其實就像是一顆焦灼之石一樣。」這裡的「焦灼」自然是因為戰火。



充滿戰禍的石頭,來自一首詩《我是一受造之生靈》[9],原文是義大利文,我把它翻譯成中文:
如同於聖米歇爾山的
這顆石頭
如此冷
如此硬
如此乾
如此無動於衷
如此全然地
死氣沈沈如同這顆石頭
我的悲傷
前所未見生者
負疚著
死亡之重
義大利跟奧匈帝國征戰其中一個戰區,那次交戰十二次、義大利死了一百萬人,後來在聖米歇爾山(也就是詩中的石頭)投放了六千顆氯氣彈(毒氣彈),幾分鐘就死了幾百人。一戰慘烈的是壕溝戰死了至少一千五百萬人,也是人類第一次投入大量殺傷力武器,如:飛機、坦克等,造成戰後極大的創傷症候群。二戰更是慘烈,有更多恐怖攻擊地方的戰爭。
閱讀此一「一切戰爭之書」會提出的問題,自然是:「為什麼會有戰爭?」對此佛洛伊德和愛因斯坦有過討論,佛洛伊德回答,戰爭是源自「死亡的欲力」,一種惡魔的印記,他認為恨是比愛更古老的關係,這種欲力會有強制重複的狀況,把所有生命強制迴轉至無生命的狀況。
畫家桑納繪製此書,把這個問題丟給我們,那我們如何面對它?未來有任何希望和可能嗎?未來會是如書末所言的「無止境」戰火的預言嗎?我反覆讀這書和一邊思考此問題,也閱讀參考關於戰爭歷史的書。發現到,儘管人類歷史是跟戰爭並生的,就如動物也會有爭鬥的行為,不過人類的戰爭的特別之處在於,會有技術的介入使用。剛開始工具比較簡單,如石器、刀劍和弓箭等,後來就越來越複雜,變成機槍、大砲、原子彈。是在工業革命之後機械化的戰爭,造成了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可怕傷亡人數和巨大的恐懼。隨著對此一技術的思索,我慢慢注意到,桑納書中描繪了手,很巨大的雙手,也是意圖掌控一切的手。
手,是人類的技術的根本關鍵,也是跟動物的差別展現,也是引燃戰火的巨大雙手。人類的戰爭之惡其實是技術之惡。人類的生存一定是離不開技術,像是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因盜取火被視為技術之神。普羅米修斯,在希臘文中是「先知先覺者」的意思,他是第一個教導人技術的人,在此詞中的「計畫、預期與控制」才是技術之惡的所在。
那時看此書時,一直在想,作為一個畫家,除了描繪此一人類戰爭從古至至今史詩般景象,讓我們可以面對此一問題去思考之外,還能有些什麼別的嗎?對此問題的思考,直到將焦點集中在「技術」上時,才獲得解答。答案其實就在眼前,在我們所看的書中所描繪的種種景象之中,具體地在於:畫家用以描繪此部戰爭之書的繪畫手藝技術上。
面對以數學、科學技術所打造出來的科技技術,畫家提供和展現出另一種技術的存在:繪畫的手藝。畫家以他的繪畫技術在對抗著科技的技術。桑納所持有的手繪的技術,這是一項在今天的數位時代逐漸遭到漠視的技術。我發現到,桑納這位作畫不打草稿的繪者,他是以「手的知性」來描繪這部戰爭史,「我始終信任在畫畫中的雙手,他們會找到最好的方式來描繪出某片天色、某座山和洶湧的海。」
最重要的是,「手的思維方向不同於心智,本性更為果敢、釋放,運作不受預定概念制約而有其靈視,它們不停地開啟、抹除、再重新啟動一幕幕的畫面,宛若沒有任何預先計畫地運作著。」畫畫的人都懂、畫下去的時候腦袋是不能有預期的。桑納說,「要信任自己的手,我們的眼睛是完美的暗房,試著畫下那些瞬間與光影的變化,不用鉛筆打草稿,也不確定是否能找到正確的色調,或是覆蓋天空、樹林和霧中房屋那層光的顏色。桑納將紙沾濕,讓光進入他的眼睛,無論色塊和記憶變化成什麼樣子,他都敞開自己去接受。」
他認為影像在心中浮現時,並沒有確切的順序;每次畫到新的一頁,都感覺自己畫下的是早已存在世界的一個影像,像是一種神祕的視覺重現。桑納在這裡提到很重要的一點是畫家正如盲人般在摸索,「我如盲人一樣畫圖,不費時間處理細節,而是尋找生命的脈動。」,為了畫這條河,自己也必須變成河,而變成河流也是某種通靈的狀況。
手的技藝與普羅米修斯的技術截然相對立。教育學家伊利奇(I. Illich)在《非學校化社會》[10]批判普羅米修斯的技術思維是將人類生活導向制度化,軍隊則是「此一制度化的荒謬體現,非學校化社會現代武器賴以保護自由、文明與生命的唯一途徑乃是毀滅自由、文明與生命。軍事術語中的『保障安全』一詞乃意味著具有毀滅地球的能力。」傳播學者麥可魯漢,也是最早提出地球村概念的人,他引用生物學家研究指出,人類自從用火以來各種日益精進的技術和人類天生的自然配備已越來愈遠。這不只導向人和技術之間的異化,更造就人和其技術之間的巨大鴻溝。
解決之道是麥可魯漢說的「我想說,藝術家的角色就是彌合這條鴻溝。」而大腦神經學家葛詹尼加(M.S. Gazzaniga)也有相同看法。他在《大腦、演化、人》[11]探討藝術時指出,人類和其他物種的重要差異在於「自由」。然而「自由是人類成功的關鍵,但是自由也是災難的邀請函。」 他指出,人類大腦的高等智商發展出一系列「可能性兵團」,這是超出人類遺傳本能,「但是,藝術填補了這個空缺。」指出藝術作為一種技藝,持有拯救被科技技術異化、乃至毀滅命運的能力。
然而藝術和身體的技藝在現代社會日益不受重視,或僅僅限於少數的人。這會使得整體社會陷入危機。手藝之人是與作為「預知者」的普羅米修斯截然相反的另一種人,伊利奇說藝術家是普羅米修斯的弟弟,厄庇墨修斯Epimetheus,意思是「後知後覺者」,在他們眼中世界是處於「未知」的狀態。所以伊利奇鼓吹著厄庇墨修斯人的再生,因為他們是「希望」的持有者,「希望,是篤信自然的善性;而期待則是意味著人所籌劃與控制的結果。」為何說厄庇墨修斯是希望的守護者?因為「未知」、「偶然」能將我們從已知、預期和控制的世界中解放出來,這也是創新的本質意涵,因此「未知」(無法預知)乃是希望之所在。就如戲劇家阿爾托(A. Artaud)說,「生命之所以值得我們熱愛,不是因為種種的預期與規劃,截然相反地:生命、生活的可貴本質乃是『未知』。」因為未知,所以能保有各種新的可能性,這也就是「尚未到來」。
數位時代的拇指姑娘[12]
—數位時代中打造技術的手更常用於滑手機
—人類獨有「拇指對掌」(opposable thumb)構造
—沒有拇指,我們就不能成為人類
—觸摸可以賦予生命
「數位時代」的英文是“digital age”,可能很少人知道“digital”的拉丁辭源派生自“digitus”,意指:「手指」;說來弔詭,數位時代中打造技術的手,更常用於滑手機。所謂「拇指世代」對大拇指的認識,是按「讚」手勢,無視那是人類獨有構造。這源自一位哲學家米榭·塞荷(Michel Serres)《拇指姑娘》[13](2012),作者塞荷說,他是在地鐵上看到一位少女靈活地以兩隻拇指在手機上打簡訊,他自認這是他「笨拙的手指永遠無法企及的」,也因此「滿懷讚嘆」。
不知是不知道或遺忘,人之所以可以以拇指在手機上靈活打字是源於人類獨有「拇指對掌」(opposable thumb)構造,和其他靈長類動物相比,我們的拇指能做出種種特技等級的動作,很輕鬆就能橫擺拇指、跨越手掌並碰觸到無名指和小指,大自然中沒有其他任何動物有「拇指對掌」構造。看似簡單卻能讓雙手有辦法抓、握、扭、轉,所以我們可以拉小提琴、畫畫,還能以其他動物不能的做法來操作和碰觸,才能使用工具、延伸手臂的力量。也就是說,沒有拇指,我們就不能成為人類。
另一本書《重返人類演化現場》[14]第三章〈發明之母〉中提到,「你的手是件出色的作品,有史以來從不曾有五根手指、十四個關節和二十七塊骨頭,以這種有趣而實用的方式組合在一起——轉動你的手,那裡有八件方塊狀骨頭在手腕裡和前臂部位以肌腱質相連,因此你才能以180度轉動手部。這樣一來,我們的手也才能做出自然界動物就算想做卻永遠做不來的事情,好比揮棒打棒球、倒一杯牛奶、演奏一曲艾靈頓公爵寫的鋼琴獨奏,或者畫一張肖像畫。」這裡也想到所上一位研究生,他有項專長,就是能夠以氣球摺出許多造型來。現在人工智慧的機器人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機器人的手可以摺氣球嗎?
這是「拇指對掌」的人類圖片[15],旁邊也有其他動物的對比,看就知道差異蠻特別的。也許你沒有仔細看過,不過一看就知道,就如沃爾特所言,「如果沒有人類的手,米開朗基羅就永遠刻不出《摩西》雕像的臉部,達文西也無法畫出《蒙娜麗莎》,鋼琴大師霍洛維茲連最陽春的《皇帝協奏曲》都彈不出來,莎士比亞也沒有辦法提起鵝毛筆書寫。」還必須指出,手是跟大腦連接的,而大腦是躲在腦殼內的,是不可能看到世界的,不過手卻直接面對世界,所以大腦的學習是依靠手而來的。手是優先於大腦,大腦的提升是根據手作為基礎的。
從手的種種研究中可以得出一項結論:製造工具不只是製作出工具來,還讓我們的大腦得以重新組構,並依雙手和世界互動的方式來理解世界。讓靈活的手指和周圍的實體對話,逐步醞釀出大腦組織、構思萬象的方式。所以想想看,當手指只能滑手機時,大腦能學到什麼?
手除了畫畫,究竟可以幹嘛?這一點我們可以欣賞Raymond Crowe的Shadow Show(詳見youtube影片)如果人類一直保有如此「手影」的技藝,世界就會是一個Wonderful world;如果人類的手只能滑手機的話,那無疑是退化的。我們的手和接觸,會是拯救之所繫。這可以從電影《瓦力》[16]的結尾看到,伊芙是透過手的接觸喚醒了瓦力。
皮膚科醫師萊曼警示,我們的社會正面臨「失去接觸」的危機。他說,我們比較習慣以手指跟手機銀幕互動,而不是給別人一個安慰的擁抱或是拍拍後背的安撫。「觸覺」這種最古老的感覺是神秘的,有時甚至難以形容,在西斯汀教堂的天花板上畫出那個神妙接觸圖的米開郎基羅知道這個道理,他說:「觸摸可以賦予生命。」米開朗基羅將自己畫在(圖23)耶穌十二門徒之一的巴托羅謬手裡所提著一張他殉道時被割下的人皮上。他把自己的自畫像畫在上面,這不正是梵樂希所言「畫家提供出他的身體」的表徵?米開朗基羅所提供出的身體,正是皮膚。

—宗教人跟藝術人同樣要具備「看不見」的能力
—對視覺中樞的大腦細胞來說,「看」到貓的強度與「想像」看到貓時的強度是一樣的
—重新認識宗教作為一種想像的強大力量和它在人類歷史上所扮演的巨大作用
這個部分主要談兩個東西:想象力的機制和瑪納(mana),在這兩點上,我們可以看到,基本上宗教和藝術是同源共生。《諸神的起源》[17]第一章開頭,作者即以猛瑪象象牙雕刻出來的「獅人」雕像,來指出人跟別的物種的差異在於想像力。作者指出,想像力,指的是會把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的能力,「獅人」並不是有「獅子人」這種動物,而是「獅子」加上「人」的想像力運作,證明了(四萬年前)人類已經具備無中生有的能力。
作者說,智人其實就是宗教人。我個人覺得宗教人跟藝術人同樣具備的一件事是要有「看不見」的能力。在英國BBC的一系列藝術人類學的影片的第二部,“The Day Pictures Were Born”(《圖像誕生的那一天》),指出史前洞穴中所描繪的動物圖像,其能力,是要以看不見作為前提。可是,大家馬上會問:看不見怎麼作畫和產生圖像?這一點,我們想想做夢這件事就知道。做夢也是閉著眼睛的,而那才是繪畫的精髓所在。
影像的產生有兩個途徑:知覺完成和觀念完成。神經學家拉瑪錢德朗(V. S. Ramachandran)為我們解釋了差別何在。他解說「看見」一隻貓和「想像」一隻貓的區別。當我們「看見」一隻貓時,牠的形狀、顏色和其他外觀會投射到視網膜,並經由視丘傳到視覺中樞,才會從視覺中樞再分成兩個通路,一個通路偵查深度和運動,讓你抓東西能夠靈活自如;另一個通路偵查形狀、顏色和認識物體。這兩個通路就是「如何」和「什麼」通路。最後,等所有訊息都統合後,腦才告訴我這是一隻叫做菲力斯的貓,並能讓我記起貓的種種,特別是關於「菲力斯」這隻貓的種種。「想像」在腦的運作與以上所說的「看見」是剛好相反的。人對貓,尤其關於「菲力斯」的所有記憶,訊息的傳遞是從上到下,也就是從高層腦區到視覺中樞把這些訊息綜合後,才能在「心靈的眼睛」看到「想像」的貓。事實上,對視覺中樞的大腦細胞來說,「看」到貓的強度與「想像」看到貓時的強度是一樣的。
在夢的強度比較高的時候,我們經常醒後會感覺到不知道那是真實的還是只是夢?英文名詞是「觀念完成」(conceptual completion),由觀念完成的形象和由(感官)知覺完成影像的強度是一樣的。這就是為什麼夢中景象會那麼栩栩如生的原因。夢中的形象或是想像活動,和我們的觀念世界有著緊密的聯繫,是觀念或說是思維活動驅使了這些形象世界的產生。
這件事情讓人驚訝地發現或是重新認識:宗教作為一種想像的強大力量和它在人類歷史上所扮演的巨大作用。這裡並非只是在講宗教的力量,而是更深入地看到「想像」的力量所在。
所謂的原始宗教就是人類最初想像力所營造出了的想像世界,換言之,想像是一種思維活動。我前陣子在看一本書叫《被隱藏的諸神》[18],是在講在中東尚存著鮮為人知的宗教,包括多種被認為早已失傳的宗教,如祆教等等。我是從文學角度去看的,書中對這些宗教教義、神話敘事等等,感覺比奇幻文學還好看、還有意思。
回到前述的想像機制,裡面有兩個重點。第一,洞窟壁畫的描繪不是在描繪外在可見現實世界的圖像,而是在描繪人們腦中的想像形象。所謂看不見的想像,這裏我可以以實際畫畫的情況作補充。我們可以觀察到小孩子畫圖時,是沒有看著實際物體、動物就能作畫。他看著的是白紙,他是依據想像機制描繪。那怕是對著景物描繪,比如我看著某人畫素描,眼睛雖然看著對方,但是當我要落筆的時候,我的眼睛所看著的是圖畫紙。所以我們等於是在「看不見」的狀況下,把腦袋中的影像運作到紙上。「看不見」這件事,不論是繪畫還是做夢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愛吃糖的恐龍
—人們是透過想像去思考世界和建構我們賴以為生的觀念
—你知道嗎?我是吃糖的。
想像力的機制還可以讓我們去了解,小孩為什麼會喜歡恐龍。也可以知道想像活動有什麼作用?也就是前述提到,將「動物」作為一種符號的思維活動的作用、功能。
為什麼喜歡恐龍?簡要回答是,人們是透過想像去思考世界和建構我們賴以為生的觀念。我們可以從孩子身上來論證這一點。孩子是人類的活化石。對動物的想像活動在孩子的世界中起著重要作用,許多原始宗教的崇拜對象也都是動物,比如部落中的圖騰動物。在這樣的想像世界中,孩子像遠古人類一樣去思考他們自身的問題,透過想像去成長、去捉摸他們身處其中的世界,恐龍就像大羚羊、野牛、猛瑪象一樣,是攫獲小孩想像力的動物符號。這首先可以從孩子的畫來看到。比如小孩畫的恐龍在打蛋,還有小孩在背上吃蛋。(圖24)或是另一幅,畫中小孩笑得很開心,因為他跟他的恐龍去散步。(圖25)女孩子也會畫恐龍,如這幅打扮非常漂亮,臉上還畫有腮紅。(圖26)



在這些畫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恐龍有如孩子們的第二自我。可以再舉個例子來說明孩子如何透過恐龍去思考。小朋友F喜歡恐龍,透過故事,他知道恐龍有分成吃草的和吃肉的不同種類。有一天他對我說:「你知道嗎?我是吃糖的。」我聽了好一會兒才恍然大悟他的意思是:他喜歡吃糖,經常要糖果吃,但是吃糖會蛀牙,所以他常常沒有得到滿足,所以他透過恐龍草食與肉食的區分系統,想像出一個他自己的系統:他是屬於吃糖的那類的生物。明顯地,小朋友F是在透過恐龍思考自身的問題,也透過這樣的想像,來定義或是說發明出自己是一種吃糖的生物,這和遠古時期或是原住民說自己是哪一種圖騰動物的後代的想法是完全雷同的。
這裡也想岔開一下,簡單說一下音樂跟出神的狀況。在出現獅人的同一時期也出現了音樂,考古材料出現了鳥骨做的古笛(詳見《諸神的起源》頁34),你可以想想,那佈滿動物形象的史前洞穴,基本上就是史前的聖西斯汀大教堂。這些洞穴並非只是繪畫的地方,也很有可能有音樂;依據考察,這些洞穴繪畫的聲音迴響相當特別。音樂學家legor Reznikoff 和考古學家Michel Dauvois合作探索舊石器時代繪畫洞穴,他們以唱出簡單音符或吹口哨的方式紀錄洞穴中的音效,發現壁畫所在位置通常共鳴特別好,原始洞穴中共鳴良好、最多殘響的地方,也是最多繪畫的地方。另一個研究也是音樂家、考古學家團隊,在西班牙北部洞穴也得出相同的結論。那些紅色圓點、線條是集中在特定區域,而這些位置通常低頻音共鳴較好,殘響適中,聲音清晰,都是演說、演奏音樂絕佳地點。(內容詳見《傾聽地球之聲:生物學家帶你聽見生命的創意與斷裂,重拾人與萬物的連結》[19],以及youtube影片:《關於古代人繪畫洞穴與音樂的關聯》,另外台大學者蔡振家的文章也可以看一下)。解開史前洞穴繪畫之謎的研究者,大衛・劉易斯-威廉斯(David Lewis-Williams),在其新近的著作,《洞穴中的心智:意識和藝術的起源》有更完整的說明。
動物是用來思考的
—從「自然」過渡到「文化」需要某種既非自然亦非文化的「消失的中介點」
—所有的奧祕來自於–動物乃是介於人類和人類起源之間的一個中介
—關於動物的思考是在動物神話、傳說等虛構敘事中去進行的
我們從哥貝力克的神廟可以看到——從天然洞穴到人工建築,等於是人們離開洞穴後,蓋起自己的洞穴。為什麼洞穴壁畫會出現動物?史前動物繪畫並非是出於單純描寫或是祈求獵捕的欲望,跟「吃糖的恐龍」一樣、是出於想像和思維活動的需求。宗教學家埃里亞德 (Mircea Eliade)認為「史前時代,人類與動物和諧地生活在一起,而且還可以互相溝通……也就是動物被所賦予的象徵意義和神祕所充滿,對宗教生活有偉大的重要性。」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 Lévi-Strauss)在《圖騰制度》[20](Totemism)提到:「諸多的自然物種的被揀選,不是因為他們適合取來食用,而是他們適合拿來思考。」動物是拿來思考的,是人類從自然朝向文化過渡的必要角色。
人出生也是動物,然後才從「自然」過渡到「文化」。精神分析學家紀傑克(Slavoj Ziżek)指出:「重點在於,從『自然』到『文化』的過渡,並不是直接的,所以我們不能在連續性的演化敘事內去解釋:兩者之間必須有某種東西的介入,即某種既非自然亦非文化的『消失的中介點』,所有演化的敘事都悄悄預設了這種中間性 (In-between ),兩者之間的「某種東西」就是動物。」藝評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為何凝視動物?〉[21]指出:「到底動物和人類相似和相異的奧祕在哪裡?所有的奧祕來自於,動物乃是介於人類和人類起源之間的一個中介 (intercession)。」
人是一種動物嗎?大部分人都會舉手贊成,可是沒有人會很高興的說:我是動物。一次通識課程中,詢問眾多大學生:「人是動物嗎?」同意請舉手。大部份人舉手,但不見欣快者。再問不同意的舉手,三、四位舉了手。詢問最前一位:「你讀哪個科系?」「生命科學系。」再問:「那你同意人是一種生物嗎?」他肯定地點頭回答:「是。」
這不矛盾。無需因為肯定演化論,而得去承認人是「動物」乃至「禽獸」。這位生命科學系的學生,肯定對人這物種的特殊性有所思考。賈德・戴蒙在《第三種猩猩》的第一個句子:「人異乎禽獸,毋庸置疑。」(“HUMANS ARE DIFFERENT FROM ALL ANIMALS”);「人與其他物種之間有道無法逾越的鴻溝,於是我們創造了『動物』這個範疇,勾畫出那道鴻溝。」也就是說,人之所以為人,乃是人將自己從他所發明的「動物」的概念區分開來才能成立。
所以前述那位生物學系的同學,很清楚人不是一種動物。伯格指出,動物所扮演的是介於人類和人類起源之間的角色,牠們既像又不像人類,牠們屬於那裡也屬於這裡。動物「既是又非」的特性因此成為人類思考自身經驗的符號。伯格指出,「人和動物的最大區別在於人類具有以符號來思考的能力。」這裡的「符號」是在語言文字之前的某種符號,比如:動物,「最早的符號是動物」。為什麼會透過動物符號去思考,李維史陀的說法是:史上第一個人要怎麼區別自身,唯有透過對動物的思考,人才能將自己從動物中分離出來。
這些想法當然不是透過動物學研究而來,而是在動物神話、傳說等虛構敘事中去進行的。圖27是大家可能還記得的波特小兔,波特小姐所畫的兔子是素描,畫面下方前景部分和周邊,佈滿寫生的兔子,而中間則是醉睡在大床上的彼得小兔。在下方的兔子與中上方的彼得小兔之間,可以看到鉛筆描繪的虛線上升並圍繞著彼得小兔,好像那是那隻閉著眼睡著的兔子的夢境。兔子是怎樣變成上方的彼得小兔呢?
在許多神話中的神祇會以各種動物的形象呈現,逐漸地動物神祇的特性就被移轉到人格神,原本鑲嵌在神話敘事的動物敘事,逐漸地轉入文學敘事領域。就像普羅普(Propp)在《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22]說,從宗教的條條框框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故事進入了另一些社會因素所推動的藝術創作的自由空氣中,因為以前的宗教敘事只有特定人士可以說,後來下放到人人都可以說,於是開始了血肉豐富的生命……一種藝術講述的起源。我們可以從狐狸的案例來驗證此一說法。可以看到在哥貝力克神廟中就有雕刻著狐狸,隨後古希臘時期的伊索寓言中也有狐狸,還有中世紀很有名的列納狐,到了1970年有達爾(Roald Dahl)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2009年則有導演有魏斯(Wesley Wales Anderson)改編成動畫電影。

瑪納一詞和其解釋機制
—「瑪納」:它保證了事物的運行機制,它使得漁網捕魚、房子堅固、小船鍾愛大海;在田地裡,它就是肥力;在醫療中,它就是拯救或死亡的力量
—人們意識並探詢著一個更深刻,超乎眼前所能見到的,一種隱藏在可見事物背後的機制的解釋
瑪納(Mana)此詞出於法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e)的《巫術的一般原理》(Théorie Générale de lamagie)[23]這個詞普遍存在於各種美拉尼西亞語(Mélanésiennes) 和大部分玻里尼西雅語(polynésiennes)中。此詞是巫術中的重要概念詞,意涵上頗為廣泛,甚至模糊不清。莫斯指出,這詞包含 「巫師的力量、某物所具有的巫術性質、巫術事物、魔法性質的存 在、具有魔法的能力、被下詛咒的、巫術行動」等等。儘管此詞 「含混不清,然而在使用上卻是相當明確。它儘管是抽象和一般的,但是又十分具體(⋯⋯)它不僅是一種力量、一個存在,還是一種行動、一種資質和一種狀態。換另種方式來說,這個詞同時 是名詞、形容詞和動詞」。[24]
莫斯說,這個詞所具有的複雜含混特性,使得人們無法對之進行邏輯分析,因此僅能滿足對此詞的各種語用狀況的描述。書中,莫斯給出了幾乎是五花八門的案例,在此僅重點指出:瑪納,這個複雜也曖昧的詞,在各種狀況中是作為一 個「解釋項」來運作。比如,瑪納用於解釋巫師能治療疾病的能力,那在於巫師具有瑪納的資質或掌握瑪納的力量或天賦,透過瑪納讓古人靈魂或自然界的精靈,成為巫術的通靈力量。簡言之,瑪納是巫師的力量的來源。又如,某些植物會使人致病,乃是「它們透過自己的瑪納成為這些不同疾病的原因。」或是「當一個人生了病,人們把他的病歸到控制他的瑪納的頭上」;也存在讓人致富的 瑪納或是殺生的瑪納等等。
莫斯指出:「由此看來,我們甚至還可以擴大這個詞的意義,而且指出瑪納是卓越特殊的力量,是事物真正的效力:它保証了事物的運行機制,而沒有取消它。正是它使得漁網捕魚、房子堅固、小船鍾愛大海。在田地裡,它就是肥力。在醫療中,它 就是拯救的力量或死亡的力量。在箭中,是它使箭得以能殺生(⋯⋯)他們把箭頭塗上毒藥,但是人們把其真正的致死效力歸結為它的瑪納,而不是箭頭上的毒藥。同樣,在鬼神精靈(démon)那裡,瑪納(⋯⋯)它看上去像是一個附加在事物身上的資質(⋯⋯)或者,換言之,像一個添加到各種事物上的東西。這種添加的部分是不可見的、神奇的、通靈的東西:總之,它是精靈,一切效力與生命都蘊涵其中。[25]
從這段描述,可以清楚看到瑪納作為一個對未知作用力的解釋項的功能。比如,儘管箭頭上塗抹了可以讓人致死的毒藥,可是當地人們卻不把致死的能力歸於毒藥,而是瑪納的作用力。這時瑪納意指的就是,那使得毒藥得以發揮其效用的化學成分,和此一成分 進入人或動物的身體之後所產生的生化機制;或是使得土壤肥沃的化學成分,如氮,或是小船在海上的種種機能與流體力學等機制;乃至,如前所提,意指偶然的運氣,那使某人得以致富的原因。簡言之,瑪納是用來指稱諸種未明力量的解釋項。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解釋運作下,當人們不將致死的效力歸於毒藥時,這表明了,他們注意到有一種不只存在於可見具體物質(箭頭、毒藥)的力量(化學成分、生化反應機制)在運作著,儘管他們不知道為何毒藥會有效力,或是土壤內的成分,或是小船的形體構造所具有與海洋相適應的力學的存在。這深刻地說明了,在瑪納一詞和其解釋機制,人們意識到和探詢著一個更深刻,超乎眼前所能見到的,一種隱藏在可見事物背後的機制的解釋。
漂浮的能指
—瑪納,作為一個沒有特定指稱對象的「能指」,乃是一個「漂浮的能指」
—神的知性是從和「所指」的不相稱的「能指」的過剩中產生出來的,瑪納就是所有神的名字
—人們發明了「神」應對人類大腦解釋功能所面對的「困窘」處境,以解釋所有未知的狀況
對莫斯的考察,李維史陀對瑪納給予更概括性的整體說明。瑪納,作為一個沒有特定指稱對象(所指)的「能指」,乃是一個「漂浮的能指」(signifiant flottant)。 產生的原因,也是這邊最關鍵的地方是從一個萬物皆無意義的階段轉變到萬物皆有意義的階段;在這次轉變之後,「整個世界萬物(Univers entier) 一下子變成「意有所指」(significatif)」。但是,人們其實並不知道真正的意義為何,人們未能在此一轉變的同時,對所有天地萬物有充分和對等的認識,到現今也是如此。人類的基本處境,從以往到現在和未來都是如此。這個處境,轉換成語言學術語來說,是能指(世界萬物意指著……)無法對等於其所指。
人掌握了所有的能指(世界萬物)一下子地掌握此一全部的能指,領悟到它們全都是意有所指的,問題在於,我們無法知道這所有的能指的所指是什麼。反過來說,認識層面的「所指」數量是有限的,相對地,「能指」卻一直是過多、過剩的。我們無法替所有的「能指」找到其「所指」,這使人類感到困窘,卻也維持著一種根本性的處境:因為它揭示著人的條件,人從一開始就掌握著「能指」的全體卻困窘於未能找到足以對應的「所指」,兩者之間有一種不相符應(inadéquation)的存在,只有神的知性(entendement)能吸收這樣的不對應;神的知性是從和「所指」的不相稱的「能指」的過剩中產生出來的。用平常的話來說,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那樣,因為平常有些事情我不知道,我就會說這是神的旨意,就是瑪納,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生病,有些人生病又好了,瑪納就是所有神的名字。
這些可以從神經學上來說明。人類之所以會認為所有具體可見的世界萬物,總是在意指著什麼,這個傾向來自左腦存在著一個神經學家葛詹尼加稱之為「解譯器」作用,它把所有感知到的資訊、現象,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一個統一一致的解釋,不管這個解釋是否是符合真實。這是一種從混亂、混沌中整理出一個秩序的功能。「解譯器」試著要從中找出因果聯繫關係,找出其背後運作的機制。西方科學跟宗教是有友好關係的,因為宗教家認為科學家幫忙了解神的運作機制,但是這到今天都無法全然做到。這就是人類大腦解釋功能所面對的「困窘」處境,因此,得發明一個像瑪納那樣的解釋項,然後以「神的知性」來統整。正是這個機制,使得人們發明了「神」(或各式各樣的名稱)以解釋所有未知的狀況。就像人們說的,事件或是某現象,乃是神意如此,其他各種鬼怪精靈或是各種神明等,也都是這個機制運作下的派生物。
說故事的大腦
—大腦是一座工廠,如果它找得到合理的解釋,就會生產出真實的故事;如果找不到,它就會製造出一套虛構敘事
—所謂的自我乃是圍繞著這個專有名詞(名字)的「漂浮的能指」所編織出來的
—專有名詞,既是語言中最具「指示性」、最具體的要素,但同時卻又是最不具指示性、最抽象、最空洞的要素
如果「說故事的大腦」不能在現實世界發現有意義的對應模式,它就會強加一套意義。簡單說,說故事的大腦是一座工廠,如果它找得到合理的解釋,就會生產出真實的故事;如果找不到,它就會製造出一套謊言(或說:虛構敘事)。說故事的大腦是很重要的演化調適,它讓我們以一種協調、有秩序且有意義的方式體驗自己生命,讓生活不只是一團鬆散、紛紛擾擾的混亂。葛詹尼加也這樣說:「這個『解譯器』的特殊系統,它會產生關於我們的感知、記憶、行動和它們之間關係的解釋。這帶來了個人的敘述性,這個故事把我意識經驗裡分散的所有方面都綁在一起,成為一個一致的整體,從混亂中形成秩序。」
葛詹尼加的說法,已經接近文學理論,自我敘事和故事編造的法則是完全一致的。就像如果你要去投考宗教研究所和去政治研究所,所寫的兩份自傳一定不一樣。自我是一種圍繞在我們名字的編造物。名字,這個專有名詞,其實就是一個瑪納,它也是一個解釋項。但,仔細想想,這個詞其實什麼也沒有解釋出來。意符就像一個遮掩物,背後其實一無所有,是個欠缺,瑪納或是其他的漂浮能指,實際上就是為了遮掩這個欠缺。
所謂的自我乃是圍繞著這個專有名詞(名字)的「漂浮的能指」所編織出來的,比如,幾乎從小到大,我們都在被詢問自己是什麼(長大的志願、自傳的書寫等等)。「自我」是我們在不同的時間點,依據所處的情境,將所有能用的經驗素材編織出來的。這個解譯器,這個幾乎不停止的編織過程,給了我們幻象。葛詹尼加指出:「人類的解譯器挖了一個洞給我們跳。他創造了一個『自己』的幻象,然後讓我們人類覺得有一個我,可以『自由地』做出我們行動的決定。」拉岡的精神分析理論更進一步指出,主體的形成有賴於意符的存在及其效應,主體只是一種意符效應,是對於一個意符的認同結果。
我們對名字的意符認同也是相同的機制:「此種根本的認同讓生命體能夠以主體的方式存在於象徵系統,並獲得一個相對於其他意符代表著主體的意符,也就是『名字』」。對精神分析來說,並非先有主體,因為主體是意符運作效應而產生的;名字、專有名詞的特性就像「瑪納」。專有名詞「既是語言中最具『指示性』(indicatif) 最具體的要素(如Jean 指的就是那個人),但同時卻又是最不具指示性、最抽象、最空洞的要素(如Jean可以是這個人、那個人或甚至任何東西)。」或是我們換個例子,有人問,「你是誰?」或你自問也可以,答案是:「我是Jean。」 但這根本沒有給出任何具體性。
這與瑪納是完全相同的。正如拉岡所言:專有名詞的作用就是為了填補空洞,讓它有個能夠封閉起來的塞子,以便讓空洞具有一個縫合的假象。拉岡說,並非他是一個個體,所以他的名字叫做雅克・拉岡,而是因為他是某種能夠欠缺的東西,所以他才需要名字來填補這個空洞。這個專有名詞,我們的名字是用來掩蓋或是縫合此漂浮能指背後的欠缺。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一直追尋自我的原因,因為自我根本上就是一種空洞、欠缺,並不是你天生個性怎麼樣的緣故。如果你天生個性就是敏捷的,那你怎麼扮演遲鈍的人?人總是在不斷編織自我敘事以回應所謂「我是誰?」的問題,也就是在這樣的自我敘事中製造出自我。
像杰羅姆・布魯納在《故事的形成》[26]說,通過自我敘事進行的自我製造是永不停歇、永無休止的。我們是通過敘事創造和再創造了自我,自我是我們講述的產品,不是藏在主體性的幽深處等待人們去研究的某種本質。就如圍繞著專有名詞,建構著無數自我敘事;而圍繞著瑪納,或是其他的漂浮的能指(不管是哪些神明、鬼怪或幽靈之名)也建構出無數的創世起源叙事、神話敘事,乃至妖魔鬼怪的敘事、傳說。
就像李維史陀說的「漂浮的能指」也是所有藝術、詩歌和所有神話性質和美學性質的發明的保證。確實,所有後來脫離宗教而獨立的各項藝術,都是和宗教信仰一起產生的,就像圍繞著我們的專有名詞,編織出關於自我的敘事,這些藝術圍繞著神之名,而編織出關於他們自己是什麼人的敘事。
漂浮的能指不一定只能是語言符號,更多的是各種物體:從宗教儀式中的各種器物和其上的紋飾、各種看不懂寫些什麼文字符咒,或各種奇異姿勢的手印等等,到會招來財運的紫水晶,乃至西班牙人用來向美洲原住民交換羊、豬的彩色玻璃珠。探問尋求解釋的本能,也可以在小孩身上看到,就是不停地詢問:「為什麼?」
漂浮的能指鏈
—帕拉維・安達巴・潘恰亞・帕-瓦
—humph變成hump
—字母表是象徵的重要交叉口,無數隱喻的出發點和匯集處,是真正詩性的途徑,通往無止盡的象徵
英國作家吉卜林在《原來如此》[27],面對他的女兒約瑟芬,這位愛發問的女孩所描述:我認識一個身材矮小的人——她有一千萬個僕人,不過他們沒有休息時間!她派遣他們出去工作,從她張開眼睛的那一刻起——一百萬個「如何」、「兩百萬個哪裡」,還有七百萬個「為什麼」!
作為作家,他深知自己是作為巫師的繼承者,選擇了以神話敘事的編造來回應「大象為什麼有長鼻子?」、「駱駝為什麼有駝峰?」、「花豹為何有斑點?」等等問題。小孩基本上就是活化石,現代人和古埃及乃至史前人類在演化上到現在並沒什麼不同。吉卜林意識到他和女兒相處對話、遊戲的整個場景氛圍是神話維度的,其中三個故事〈第一封信怎麼來的?〉、〈字母是怎麼來的?〉 和〈禁忌的故事〉,其時空背景就是設定在新石器時代。這本翻譯成中文僅有200頁出頭的小故事集只有12則篇幅不長的故事,但是令人很難以相信地,它幾乎涵蓋了世界五大洲和召喚東西方和非洲、澳洲和大洋洲等地的神祇,來進行其神話敘事,幾乎是一本小小的世界神話學了。關於世界創生或剛形成的場景,更涉及多方神靈、宗教和巫術、還有《聖經》、《可蘭經》、印度教史詩、阿拉伯神話,也使用從古代的北歐盧恩文、埃及象形文字。吉卜林在裡面也模仿各宗教文化的圖畫和自己配上相關插圖。我想巫師向來如此,能自創敘事(神話、詩歌)和創制咒語、繪畫、藝術,這點應該從史前洞穴的繪畫和前述的哥貝克力神廟就給出強力的明證。這本書我想或許宗教所同學們可能也會感興趣。
在此我們要集中討論其中一篇,〈駱駝的駝峰是怎麼來的?〉 的一個情節,去看其中用來召喚神靈的漂浮的能指的使用。那時世 界剛被創建,人和動物都忙著整建的工作。不過,只有駱駝不願意 工作。大家去問他要不要來幫忙,駱駝總是高傲地以「哼!」不屑 地回答。大家很生氣,決定召喚掌管沙漠的Djinn神來處理。他們 怎麼召喚呢?
中譯文指出,他們在「沙漠邊緣召開了一次又一次的會議」,然而原文中,這是四次會議,每次會議,吉卜林都使用了外來語和異國語言:第一次的「會議」使用“palaver”,這是來自葡萄牙的外來語,原意指「言辭」,進入英語中,指「閒談、聊天、廢話」和「恭維」還有「大驚小怪」和最後一種罕見用法―「不同 民族間不協調的交涉、商談」。第二次的「會議」使用“indaba”,這是南非的Zulu-Bantu語,指「重要會議」;第三次的「會議」使 用“punchayet”,這是印地語,印度北方方言,後來成為印度官方語言,意思也是會議。最後使用“pow-wow”,此詞更特別了,是居住在加拿大北方的原生印第安人阿爾岡京族人(Algonquin) 的語言,意思也特別,指「魔法儀式」。然後,經過這四次極為怪異的語言的會議之後,召喚來的是Djinn神,往昔穆斯林信仰中的神靈(其實就是後來的神燈精靈),在文中吉卜林將之轉換成沙漠之神。要注意到,在英文單行的普及版中,這些辭彙都沒有任何註解)中譯本則是採取意譯的方式,完全省略了奇異語音的效果)。而且還要注意到,這四個詞彙對吉卜林的大女兒來說,是完全不解其意的,因此就只剩下奇異的語音效果。這些外來奇異語音文字的使用,為的是什麼作用? 答案是:咒語。
這是唯一的解答。四次會議,直接替換成四個奇異語音的外來語言,連著念起來就是:“palaver-indaba-punchayet-pow-wow”,試著 音譯成中文:「帕拉維-安達巴-潘恰亞-波-瓦」。放回原文,英文是:“they held a palaver, and an indaba, and a punchayet, and a pow- wow”,這裡我們還須注意到“held”和“hell”的諧音聯想,後詞在口語中放在句首,表示憤怒之意,而他們在此召開會議,便是對駱駝的懶惰和不聽規勸和態度傲慢深感憤怒,所以,若試著翻成中文,可意譯成:「他們憤喊著帕拉維,和安答巴,和潘恰亞,和波-瓦。」這完全是一句標準的自創咒語。我們還須注意到,四次會議的第一個詞,在葡萄牙文中就是指「言辭」,不過此時則成了「咒語」:從第一個詞,「言辭」到最後一個詞,就成「魔法儀式」。
藉由這些奇異語音的外國語言,將之轉換成自創咒語,為的 就是召喚緊接著出現的Djinn神。這個語音的魔術尚未結束。Djinn 神來了之後,他也是透過語音的咒語,讓駱駝長出駝峰。每次駱駝 回答沙漠之神的責問時,都一貫高傲地只回答:「哼!」原文中 使用擬聲詞“humph”,而魔法就在這裡,隨著不斷的“humph-humph- humph”,“humph”就變成了“hump”,即「駝峰」。將 “humph”變成“hump”,也如拉岡所言:「是語詞的世界創造出事物的世界。」[28]
以上對吉卜林自創咒語的分析,更可以看到在語言的運用上 面,在神話和故事中,其運作和效用都是一樣的。對語言作為神話 的密碼的解讀,卡西勒(Ernst Cassirer)在《語言和神話》中有很好的說明。他指出有一種「神話製作意識」(mythmaking consciousness), 這個概念的意思是:「名稱不僅指稱其對象,而且就是其對象的實質;實在之物的潛能即寓於其名稱之中。」他以古希臘神話的解 讀來說明:「丟卡列翁(Deucalion)和皮拉(Pyrrha)的傳說:當宙斯將他們兩個人從毀滅了人類的大洪水中救出之後,他們從地上撿起石塊,拋擲身後,石塊落地變成了人,他們倆人也就成了新人類的祖先。這種人由石塊變成的起源說確實荒誕不經,似乎也無從解釋。但是,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在古希臘語中,人和石塊是由發音相同,至少也是發音相近的名 稱所指代的,“ λαοi”[laoi]和“ λãας”[laos]二詞[29]是半諧音 詞,問題不是即刻昭然若揭了嗎?」[30]
吉卜林對於文字作為一種創生的魔法知之甚詳。在〈字母怎麼來的?〉,他創制了發明字母的敘事。故事中父女(特古邁、塔菲)在發明完字母之後,「特古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製作一條刻有所有字母的魔法項鍊。」那是一串以麋鹿牙齒、舊象牙、牡蠣 殼、蚌殼、銀線、公鹿角、有黑漆的木板、大瑪瑙貝、珠母貝、銀製魚叉、薄片骨頭、斑岩、乾燥的響尾蛇的尾端響環、珍珠母、石榴石和綴以許多黑珍珠、陶珠、小銅珠、小象牙、非常古老的非洲珠子和一顆大銀珠的字母項鍊,重達「一磅又七點五盎司」,整個 製作時間則「耗時整整五年」。這條魔法字母項鍊,後來也真的打造出來。
我們應當注意到,這樣的字母項鍊,是一種文字畫,一種「符號–意象」(signe-image)或「符號–物體」(若以打造出來的實體項鍊來說),而其魔力也在此。在〈禁忌的故事〉中,塔菲可以用這條字母項鍊來施咒(製作禁忌),比如將項鍊放在某物體上,就沒有人可以碰觸它:或是將項鍊掛在花園門前,防止有人進 入,或其他禁制令。這樣的字母項鍊其實是脫離語言學用途的,也就是說,不是服務於組合成某一詞語:它持留在其自身。
羅蘭・巴特在〈字母的精神〉指出,字母自然可以組成文字、句子等等,但是它們自身(字母表)可以組成語言學之外的「別的東西」,字母表是一個獨立系統,一個功能、技術場所(lieu technique)都無法窮盡的物體(objet),這是一個能指鏈(chaîne signifiante), 一個在意義(sens)之外,,但不是在符號之外的音義段/意群(syntagme)。這段在意義之外卻具有無窮盡的指稱的音義群,可以指稱什麼?巴特說,作為符號-意象的字母表,具有「多義」polysémique,甚至是「泛義」pansémique 的本質,「它從語言學的作用功能解放出來後,可以去說一切。」巴特在另一個出處說:字母表是「象徵的重要交叉口,無數隱喻的出發點和匯集處,是真正詩性的途徑,該途徑不通往話語、不通往邏各斯(logos)、不通往系統,而是通往無止盡的象徵。這一點和前面說的瑪納或是漂浮的能指,是完全相同的。字母和圖像的鏈結——正如在那串字母項鍊表明的那樣,那是一串「漂浮的能指鏈」,我們在這裡又看到了李維史陀所提出的 「漂浮的能指」作為神話虛構、藝術和詩的根源地。
老虎和Gojgam的故事
—天啊!Gojgam是什麼,這麼厲害?
—是先有了語音(能指)而非先有了意義,兒童才去尋找探索其相應所指。
我們也可以從民間故事來看漂浮能指的運作。依據普羅普,民間故事是從往昔的神話故事流落到民間後形成。這裡要看的案例是韓國的民間故事:老虎和Gojgam的故事。這故事是講有個村子經常發生老虎吃小孩的故事。有一天,老虎又下山来、跳進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那家小孩不知道為什麼正在哭哭啼啼,小孩的母親就對他說:「你再哭山猫就來了」。老虎在院子裡聽到,很不屑地搖搖頭–山猫算什麼嘛!小孩還是哭,母親又說:「你再哭野狼就来了」,老虎一撇嘴–野狼算什麼嘛,你說我的名字他就不哭了。小孩還是哭,母親就說:「你再哭老虎就来了」,老虎在外面點點頭,小孩很不給老虎面子,還是繼續哭。母親於是就說:「你別哭了,Gojgam 來了!」孩子竟然馬上不哭了。於是老虎想:「天啊!Gojgam是什麼,這麼厲害?」
村子裡有個偷牛賊,常在晚上出來偷牛。這時偷牛賊剛好要來偷這戶人家的牛,他爬上牆頭看到老虎的影子,以為是這家人没把牛關好,喜滋滋地就往老虎背上跳。老虎正在想著什麼是Gojgam,頓時魂飛魄散,大吼一聲:「啊,是Gojgam 來了!」偷牛賊還沒回過神来,本能地死命抓住老虎的尾巴,老虎想甩掉 gojgam,却怎麼也甩不掉,不敢回頭,只死命地往山裡跑。偷牛賊後來終於看清自己抓的是老虎,嚇得滚了下來,被人抓住。而老虎因為害怕 gojgam,從此再也不敢下山來。 Gojgam對故事裡的老虎來說是聽不懂的人類的能指;但gojgam,在韓文裡指的是「柿餅」的意思,是媽媽後來受不了小孩的哭鬧,給小孩吃的柿餅的意思。自然,我在此講述時,特意只使用了柿餅的語音,這樣一來,就能凸顯其純粹語音所給出漂浮能指的效應。

兒童學習語言的根本機制是語音
—兒童語言學習的重點不在於了解系統的詳細內容,而是知道「語言」作為一個系統的存在
—是先有了語音而非先有了意義-兒童才去尋找探索其相應所指
瑪納或是意符的機制,遠遠不僅是前述所提到的關於神話創制或是咒語的製造,其機制更重要的,其實是揭露了兒童學習語言的根本機制。我們都知道幼兒是語言學習的天才,兒童到底是如何學會語言的?日本語言發展學家今井睦美,在《哎唷!牙齒「踩」到嘴唇?揭開兒童學習語言之謎》[31]就對兒童如何學會語言的兩難困境做了剖析。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小孩子是先知道「意義」,只要再連接到適當的詞語,就等於「習得到詞語的意義」。比如很多人以為小孩子先知道「紅色」的意義 (給他看紅的東西)然後再連接到「ㄏㄨㄥ ㄙㄜ」的語音。但是從「語意系統」的觀點來思考語言的意義,就知道學習詞語並不是這麼簡單。這個意義先於語言的假設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兒童一開始當然無法掌握語言系統的全貌,兒童必須掌握系統全貌才能理解每一個單字的意義,但另一方面他又無從窺知系統全貌。
剛學會說話的小孩不僅對語彙系統的全貌一無所知,甚至連其中一小部分也不知道。如果不知道整體,應該就無法學習單一的要素,然而如果沒有累積要素,就無從掌握全貌。兒童是如何跳脫出這樣矛盾兩難局面呢?他是如何知道他所面對的、不知道的語音卻能連接到不知道卻知到意有所指呢?今井美說兒童語言學習的重點不在於了解系統的詳細內容(和其所有相應關係),而是知道「系統的存在」。這個系統就是「語言」。
兒童的兩難困境和其解決方式,其實非常類似前面李維史陀所描述的,人們發現到世界萬物總是意有所指的處境:人們知道某事物現象,比如雲的濃密顏色意味著暴雨,或是雨後會出現彩虹等等,也就是說,現象之間有其相互關係,而且它們彼此還構成一個整體的系統。兒童面對(聽到)圍繞著他周圍的母語的各式各樣的語音,是先辨識出母語的特有音位(每種語言有其特有的音位)並瞭解到各種語音是屬於「語言」系統範疇的 (非一般聲響噪音),從而理解這些語詞(音)是「語言」,是總有所意指,並且歸屬於語言系統。
因此,是先有了語音(能指)而非先有了意義,兒童才去尋找探索其相應所指。拉岡同樣指出,兒童學習語言的過程,並非一點一滴去學會使用成人的概念,而是他們一開始就獲得大量的意符,進而透過這些意符去衡量、探索週遭的世界。此外,「人類思想之所以能夠發展,並非因為『擁有』語言,而是『為了』語言。因為人類必須經由智力的探索,才能獲得意符與概念之間的連接。」
這裡的「擁有」指的是已經知道語言意符的意涵,然而人們並不知道,因此是不擁有的;而「為了」,指的就是先有意符,「為了」去探明理解意符的所指、意涵,才發展出思想。哪怕「表面上看似沒有意義的語句,只要被『表達』出來均會有所『意謂』。」我們可以想想某些現代詩中的詩句,或是道士在畫符,你覺得那是沒有意義的字句,仍有它的效用。這是拉岡前面所提的「一開始就獲得到大量的意符」但並不知道其所對應的所指,和李維史陀所言的「過剩的能指」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參閱影片:《歸因理論的謬誤》、《兩個雙胞胎小孩的互相模仿的過程》)
星座與咖啡
人們運用他們已經知道的少數相關性,從中建立某種模式,並且將這種模式運作到其他新的,或是尚未知道的狀況去進行解釋,去推測未知現象的意涵。自然也從中產生出許多解釋性的敘事,諸如各種解釋世界創生的神話敘事。比如幫天上的繁星命名,從中看出熊、獵人等,並建構出一系列神話敘事,更進而建立星星的移動與君主、國家 或個人的命運的聯繫,乃至國族神話(包含史學或是龍的傳人等)。還有各種宗教敘事和各種妖靈鬼怪故事,也都是不同的「漂浮的能指」的建構物。除了社會層面,也會延伸到日常生活各層面,比如說星座,現今依舊有人每週看星座預言;就連喝杯咖啡也可以,比如土耳其咖啡,每次喝完都會有不同的殘渣,有人就用它編織了一套占卜的系統。就算不進行這類占卜活動,我們依舊會在生活大小事情中,尋找或是「發現」各種所謂的徵象,或是配戴一些小信物等等。對這些活動,也常成為小說、電影的主題,比如法國導演侯麥(Éric Rohmer)的著名電影《綠光》就也很好的呈現。
安柏托艾可的《玫瑰的名字》
—「玫瑰」是一個漂浮的能指,一個瑪納,一個專有名詞,一個虛名
符號學家安柏托・艾可的第一本小說《玫瑰的名字》[32]更是知名案例。這部小說是仿效柯南・道爾的人物配置,福爾摩斯和助手華生。書中的福爾摩斯是威廉修士,他的助手則是位見習僧阿德索。他們在追尋一起連續七個人死亡殺人案,然後發現有著《默示錄》(《啟示錄》) 七聲號角的徵兆。追查的結過,最後發現並非如此,儘管他們依照著《默示錄》給出的線索(藍圖)去探詢。
小說最終找出了兇手和殺人的動機。其中,威廉修士和阿德索有數頁關於「真理」對話。威廉對阿德索說,我從未質疑過符號的真相,那是人在世界上賴以判別方向的唯一依據;我不理解的是符號之間的關係。他接著說,我之所以追查到佐治(兇手),是依循看似符合所有兇案特徵的〈默示錄〉模式,但其實那一切全屬偶然。然後是追查到喬治亞,因為我始終在尋找要為所有兇案負責的單一兇手,結果卻發現每一個兇案的兇手都不同,甚或沒有兇手。追查佐治,是因為威廉相信有一個邪惡的慎密藍圖,但其實根本沒有藍圖,或應該說就連佐治也被他自己最初勾勒的藍圖所害,才引發了一連串的因、連帶因以及相互矛盾的各種因,卻自行發展,以至於中間的關係脫離了任何一個藍圖。威廉說:這與我的睿智何干?我只是鍥而不捨,追查秩序的假象罷了,但我早該知道宇宙中並無秩序可言。不管是信仰堅誠的阿德索,或是我們一般凡人,人類向來難以接受一切都僅是偶然,在眾多跡象的背後,並無意義或真理——就如愛因斯坦面對量子力學而說的那句名言:「上帝不擲骰子!」對此,波耳說:「愛因斯坦,請別指導上帝該怎麼做!」
威廉的話和隨後的思考,阿德索在靜默中體會到:「墜入靜默空無的神性之中,那裡既無善工,亦無心象。」在《玫瑰的名字》這部偽託為手稿的小說最後〈末頁〉寫道,「寫字間好冷,我的大拇指好痛。我留下這份手稿,不知所云,不知給誰,昨日玫瑰徒留名,吾等僅能擁虛名」。
這偵探小說中的情境,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面對世界萬物,並將之視為總是有所意指的世界;人們探尋其中,探詢著符號與符號之間的諸多關聯,並預設有著整體意涵,期待背後有個最高者籌劃著一個縝密藍圖,堅信我們的存在是必然,而非偶然、隨機。 我們也因此相信自身有一主體,而非諸過往經歷的隨機碰撞自行發展的結果。然而,艾可透過小說指出:「吾等僅能擁虛名」,此名,乃是玫瑰之名。艾可曾經解釋,為什麼選擇這個書名:「因為玫瑰這個象徵物的涵義太過豐富以至於形同闕如」,「玫瑰」是一個漂浮的能指,一個瑪納,一個專有名詞,一個虛名。
最後做個結語。人類具有兩種手,這兩種手也對應著兩種神的形象。第一種神和手的形象是技術,從工業革命以來的各種工廠、機器、武器和交通、影視媒介、電腦數位技術、人工智慧、虛擬裝置到生物遺傳操作等。這樣的「技術」既是強大力量同時也可能帶來人類毀滅。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技術與時間1》指出「當代技術的悖論」,「技術既是人類自身力量,也是人類自我毀滅的力量」,他所說的毀滅威脅,不只有核子戰爭、生態危機、遺傳操作,還包含「知識消亡的威脅」,這是指電腦與數位技術帶來的各種「知識的代理」。
更往深層探究,這種種乃自從文藝復興之來:以全面化的數學-計算為基礎而開展的技術。數理空間的透視法、數學作為科學的語言——伽利略所言,自然這本書是以數學語言所寫就——還有奠定資本主義的複式記帳,乃至到今日的數位世界。這種種乃是基於數學,或是精確計算、算計-預期的掌控一切的技術。這種種也是前述斯蒂格勒所言的當代技術的悖論困境的背景。
這樣的技術能力,讓就如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在《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Sapiens, A Brief Histoire of Humankind)所試圖去思考的:人類這個物種,在數千年歷程之後,朝向著「扮演上帝」的角色。而在此,我們想要聚焦思考的正是哈拉瑞所指出的「變成神的這種動物」的概念。必須指出,在哈拉瑞所言的「神」,事實上是立基在前述文藝復興之後西方科學發展,隨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張的基礎上,也是如此文力圖說明的是,是企圖預期掌控一切的主宰精神。
此外也必指出,形而上學或是說宗教、神的概念,其實並未在啟蒙運動之後,在所謂科學昌明之後退位或消失。事實上相反,科學與技術(數學–數位化)和金錢、資本,成了新的神,成了現代的形而上學——此際,突然冒出一個疑問,資本主義或是科學技術,是否有被納入宗教學研究領域呢?
然而存在另一種神的概念,就如有科學數位技術之外的技術。這另一種神,可以從法國作家讓・紀沃諾於1953年,在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所書寫的《種樹的男人》(L’homme qui plantait des arbres)。這個作品廣為人知,有有高達50、60種語言譯本,國內就有好幾個譯本,最早似乎是森林學家金恆鑣(1997,時報)的譯本。[33]出版後,更有弗烈德瑞克.貝克(Frédéric Back)於1987年繪製的動畫。此作品引發各地推廣植樹的運動與風潮。[34]台灣後續的譯本中也收錄了在台灣實際持續種樹的案例,如詩人吳晟和更知名的賴倍元先生還有持續救樹護樹的十呆基金會的老樹媽媽謝粉玉女士等。
故事內容:一位居住在法國的維赫農地區的55歲名叫布非耶的獨居牧羊人,他以一人之力,每天種下一百棵橡樹種子,持續數十年,期間還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最後將整片荒地開墾成綿延數十公里,寬三公里的森林。森林還使原本乾枯的河床重新成為溪流,也使得廢棄的村莊再度成為美麗的莊園,後來這片森林更被法國當局列為保護區。而布非耶最後以89歲的高齡病逝於當地的巴農安養院。這故事甚為知名,這裡僅簡要召喚一下。我們於此想要聚焦處理的,首先是這故事,對前述持續種植並使荒漠恢復生機蔚為成林的事蹟,作者透過故事陳述者對此為種樹的男人,布非耶,的描述,其次是紀沃諾這個作者和其和平主義立場。
一開頭,就指出一個真正品行出眾者,其要點在於,不為己私沒有存著任何回報,並能在「大地上留下具體可見的印記」。[35]這一點讓我們想起紀沃諾,從未收取此一高印量作品的任何版稅。[36]此外,此作品也影響了許多人開始去種樹,自然這也在大地上留下具體可見之印記。其次,布非耶的種樹行為,確實完全不是什麼計畫和預期掌控性質的行為。他並不知道他所播種的土地是屬於誰[37],再者,陳述者指出:「他並不在意他的行動會帶來什麼結果,他只是一意執行他的任務。」[38]這標示出,種樹者,並非普羅米修斯之人,不是預期掌控,而是期待,就如伊利奇所言的厄比墨修斯之人。如故事中所言,持續種樹,「引發一連串效應」:「幾條小溪裡有了水流(⋯)一有了水,柳樹、燈芯草、牧園草、花園和花朵也一一出現,展現了生命的意志。」[39](《種樹的男人》,p.31~33)
最後,最重要的一點,陳述者,或說是見證者,在兩處以「神」來比喻此種樹男人之作為。一處,在陳述者一次世界大戰——「見過太多人死於戰場」——結束後,他回去探看,那時,從1910年種下的橡樹已經十年了,森林已經全長達11公里,最寬處有3公里。此時,陳述者說:「當我們意識到這一切都是出於這個人的雙手和心靈,沒有任何技術支援,我們便能明白世人除了破壞力之外,在其他方面也能和上帝一樣有效率。」另一處在故事結尾,在以《聖經》中的「留著牛奶與蜜的迦南地」來比喻這整片重獲生機的土地之後,在最後第二段,陳述者:他「對這位沒有文化教養的鄉下人非常尊敬,他懂得做一件只有上帝可比擬的工作。」這裡非常明確地表明這樣一位種樹者,一位農夫,所做的事乃是可堪與神相比擬之事。
所以,紀沃諾在此故事中明白地揭示,有一種重要、珍貴地,並且完全不同於我們前述所指出來的奠基在技術掌控的萬能之神,之外的神性存在。而此一神性可以展現體現於一個所謂沒有文化的農夫身上。
紀沃諾書寫此故事,是在1953年。那時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而在一戰之後,這位讀書只有到高一就輟學的作者,目睹殘酷的殺戮和好友、戰友的死亡而成為堅定的和平主義者。我們知道一位堅定乃至徹底的和平主義者是絕不使用武器與暴力,也拒絕兵役。1939年他就因為反對全國總動員,到處張貼「反對」的傳單,而被捕入獄。在更早前,1937年一月,他發表《拒絕服從》,同年九月,他更說出讓法國舉國譁然的話:「我情願做一個活的德國人,不願做一個死的法國人。」這堅決表明其和平主義的不抗戰決心。而書寫此文之前,紀沃諾還因二戰結束後被誣告以「通敵罪」而被關押五個月,其作品在法國禁止出版。
《種樹的男人》可以說是,紀沃諾對兩次大戰的經歷與省思下產物,在此作品中,如前述,反對掌控宰制的技術之神,反對此一僭越之神,而揭示一個不僭越、不預期的神性表現。人的神性,完全可以不是如哈拉瑞或是寄望於透過技術與經濟算計之下的萬能技術之神,而是可以是這位種樹者,一位懂得實踐神可堪比擬工作的人。
紀沃諾此文僅管引用了《聖經》的迦南地的比喻,也明白地使用了「神」(Dieu)一詞,然而,這樣的「神」,是某種相當「異端」的說法,就如紀沃諾所偏愛的對大自然和萬物還有對農夫,耕作者的喜愛乃至信仰;他將「神性」概念移置到如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在《匠人》所言的“Animal laborons”,這樣一位幾乎不言語持續堅持數十年勞動者身上。此一勞動之人也是如桑內特所推崇的匠人,持續不斷地工作勞動的工藝之人。在紀沃諾此篇故事中,其神性,遠非如基督宗教經典中的上帝形象,那位可以在六天創造世界的神。不是於短瞬時間將荒漠變為森林的神,而是持續數十年不間斷辛勞工作所造就。
最後我們看兩個畫面中呈現的手。一個是桑納在《如同此石,一切戰爭之書》中所描繪的巨大宰制的手;另一個是美國木刻版畫家麥克爾・馬可帝(Michael McCurdy)為《種樹的男人》創作的在播種的手。那是以木口木刻版畫(wood engraving),這是一種比傳統木刻版畫,在雕刻技術上更為費力的技術一刀一刀雕鑿出來的圖像。

在馬可帝的版畫中,給我們繪製了在種植的手的圖像。我們可以將此一表徵著栽種、文化——我們知道“culture”一詞就是源自動詞,栽種、培植——和手藝的手和桑納在《如同此石》中描繪的那雙掌控主宰人類的手的圖像比對細審。從這兩個圖像我們可以看到預期與宰的手和栽種的手是多麼不同的意象,也在這兩個意象後面連接著兩種不同的「神」的概念。後者之手,此一手藝者之手,才能將我們從我們身陷其中的技術悖論解救出來。
最後一則故事來作為這次分享的結束。不是瞬時創造的全能之神,而是強調堅持工作的勞動、工匠之神。這讓我們想起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世界與褲子〉這則小故事。貝克特在《終局》(Endgame, 也是棋局中「殘局」之意)——紀沃諾在二次大戰之後書寫,那時整個歐洲也如一盤殘局——中講述了這個故事,摘述如下:
一個英國人,想做條長褲以便過新年時穿,於是,他去找了裁縫師量尺寸做褲子。裁縫師說,「好了,可以,四天後來拿,到時應該就做好了。」四天後,顧客去拿褲子。可是裁縫師說,「抱歉啊,褲子後檔還得再修,八天後再來拿吧。」八天後,顧客再去拿褲子。裁縫師說,「真對不起啊,褲檔部分有點不合,得十天後才會做好。」無奈,顧客折返,十日後再回。此時,裁縫師說:「十四天後再來拿吧,前檔部分還得重縫。」如此這般,三個月過去了,顧客再去取褲子時,裁縫師又說,扣眼沒對得很好。
這時,顧客吼道:「該死的,這在搞什麼!先生,六天!上帝就創造了整個世界。而您,三個月做不好一條褲子!」裁縫師:「先生啊,先生啊,您看看——(輕視的姿態、嫌惡語氣)——這個世界⋯⋯再看看——(充滿感情的姿態、自豪語氣)——我這條褲子[40]![41]
以上,謝謝各位。
參考資料
[1] 人本教育基金會出版品。
[2] 《許多孩子許多月亮》,藍劍虹,晴天出版社,2009年。
[3] 《許多孩子許多月亮》,藍劍虹,東方出版社,2017年。
[4] 《可不可以畫》,藍劍虹,晨光出版社,2022年。
[5]《獵托邦傳奇》,文/劉美瑤,圖/藍劍虹,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出版,2011年。
[6] 《眼與心》,梅洛龐蒂著,龔卓軍譯,典藏藝術家庭出版,2007年。
[7] 藍老師在《童里專欄》的三篇文章:〈Digit與手,數位圖像時代下的技術反思——我們遺忘了什麼〉(上、中、下),關於手、觸覺與認識、觀看、體驗世界的關係有更完整的描述與反思。
[8] 從石頭到核武,一部人類戰爭史的縮時景象──7個角度解讀無字繪本《如同此石:一切戰爭之書》。
[9] Giuseppe Ungaretti 是二十世紀義大利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出生於埃及亞歷山大,〈我是-受造之生靈〉(Sono una creatura)是他在1916年、一戰期間所撰寫,當時詩人身處聖米歇爾山、義大利軍隊正在部署與征服該地。
[10]《非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Ivan Illich著,吳康寧譯,桂冠出版,1992年(已絕版)。
[11]《大腦、演化、人:是什麼關鍵,造就如此奇妙的人類?》,Michael S. Gazzaniga著,鍾沛君譯,貓頭鷹出版社,2020年。
[12] 藍老師在《童里專欄》的三篇文章:〈Digit與手,數位圖像時代下的技術反思—我們遺忘了什麼〉(上中下),關於手、觸覺與認識、觀看、體驗世界的關係有更完整的描述與反思。
[13]《拇指姑娘》,作者漢斯‧克利斯蒂安‧安徒生,繪者,趙燕(筆名:剛果 ),含章有限公司出版,2012年。
[14] 《重返人類現場》(簡體書),沃爾特著,三聯書店出版,2014年。
[15] 拇指是手中最靈活的部分,詳細的解說請參閱維基百科「拇指對掌肌」辭條解說
[16]《瓦力》(WALL-E,香港譯《太空奇兵·威E》)是2008年一部由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華特迪士尼影片發行的電腦動畫科幻電影。故事描述地球上的清掃型機器人瓦力愛上了機器人伊芙後,跟隨她進入太空歷險的故事。請參閱維基百科「瓦力」辭條解說。
[17]《諸神的起源》,Neil MacGregor著,余淑慧譯,聯經出版公司,2020年。
[18]《被隱藏的眾神:一段在中東尋找古老智慧的旅程》,Gerard Russell著,葉品岑譯,八旗文化出版,2021年。
[19]《傾聽地球之聲:生物學家帶你聽見生命的創意與斷裂,重拾人與萬物的連結》,David George Haskell著,陳錦慧譯,商周出版,2022年。
[20]《圖騰制度》(簡體書),李維史陀著,梁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1]John Berger著,劉惠媛譯,〈為何凝視動物?〉,《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22]《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俄]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著,賈放譯,中華書局出版,2006年。
[23] 此論文收錄於Marcel Mausse,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récédé d’une Introduction à l’œure de Marcel Mausse par Claude Lévi-Strauss, éd. Quaddige / PUF, Paris, 1950. 中譯本:《社會學與人類學》,馬塞爾・莫斯,佘碧平譯,上海:上海 譯文,2014。
[24] 以上引文參見Marcel Mausse,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前引書,頁101-102。
[25] Marcel Mausse,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前引書,頁104。中譯文翻譯有參考 自兩本中譯本:《社會學與人類學》,馬塞爾‧莫斯,佘碧平譯;《巫 術的一般理論 獻祭的性質與功能》,楊渝東、梁永佳、趙丙祥合譯,廣 西師範大學出版,2007。
[26]《故事的形成:法律、文學、生活》,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著,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年。
[27]《原來如此的故事》,拉雅德.吉卜林著,游紫玲譯,玉山社出版,1998年。。
《原來如此》,拉雅德.吉卜林著,張惠凌譯,晨星出版,2005年。
[28] Écrits, Jacques Lacan, Paris, éd. Seuil, 1966, p.276. 中譯本參見《拉康選集》,褚孝泉譯,上海:上海三聯,2001,頁287。
[29] λαοi是ληόζ(人民、民眾士兵軍隊)的複數型態,指:「臣民、子民」; λᾶοζ是「石頭、石塊、岩石」,參見《古希臘語漢語詞典》,羅念生、水建馥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494、頁498。兩詞發音音標部分為筆者查對添加,參見The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網站。
[30] 《語言與神話》,恩斯特・卡西勒,于曉譯,臺北:桂冠,1990,頁5。
[31]《哎唷!牙齒「踩」到嘴唇?揭開兒童學習語言之謎》,今井睦美著,黃涓芳譯,貓頭鷹出版社,2015年。
[32]《玫瑰的名字》,安伯托‧艾可著,倪安宇譯,皇冠出版,2024年。
[33] 此譯本附有其兄金恆杰(金載熹)法國文學研究者、翻譯家所寫的〈讀者文摘不知道的事(跋)〉。此文詳細說明了《種樹的男人》出版時背後的故事,可惜後續譯本就未再收錄此文。
[34] 比如當時出版此書的切西爾古松出版社還加入美國林業協會的「全球綠化」計畫,提撥此書收入百分之五捐助,更設立「紀沃諾獎」頒發給每年個人植樹的最高成就獎。參見:《種樹的男人》,讓・紀沃諾(Jean Giono),金恆鑣譯,台北:時報,1977,頁9~10。
[35] 《種樹的男人》,讓・紀沃諾(Jean Giono),邱瑞鑾譯,台北:果力,2015,頁7。
[36] 「凡有人要出版我這篇東西,我一律不收版稅。有個美國人來看我,要求我准他印十萬冊在美國免費贈閱(我同意了)(…)這篇東西是我所寫過覺得最自豪的文字之一,它雖然沒有為我換來一分錢,卻正因為如此,它完成了我為它而寫的使命。」《種樹的男人》,讓・紀沃諾(Jean Giono),金恆鑣譯,前引書,頁64~65。
[37] 「我問他,這是他的地嗎?他說不是。那麼他知道這是誰的地嗎?他也不知道,他猜想這是公有地,或者是地主廢棄不管的的私地。」《種樹的男人》,讓・紀沃諾(Jean Giono),邱瑞鑾譯,前引書,頁21~22。
[38] 同上註,同書,頁31。
[39] 同上註,頁31~33。
[40] 原文每個字母大寫:PANTALON。
[41] 概述引自《終局》法文版(Fin de partie),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57, pp.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