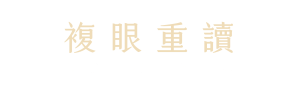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吳明鴻(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候選人)
身體的差異生產:論踏實、努力與徹底[1]
……我寫小說,很多是從每天早晨練跑路上學到的,很自然地從肉體上、實務性地學到。可以把自己嚴格地逼到什麼程度,到哪裡才好?休息多久算正當,超過多久算休息太久?到哪裡是適當的一貫性,從哪裡開始會變偏狹?外部的風景必須意識到什麼程度,對自己內部要深入集中意識到什麼程度?要相信自己多少?要懷疑自己多少?……(村上春樹 2008: 96)
對於我這個鎮日面對學位論文的爬坡人而言,這段引文可謂字字珠璣、深得我心,每一句都是我無時不在面對的課題:對自己「嚴格」是必要的,但一旦過度了就會潰決;「休息」是需要的,但休息太久就會鬆弛、再難集中心志;「適當的一貫性」對學術文章來說實屬必然,但一不小心就會過度形式化而陷入「偏狹」的危險;「外部風景」對我來說意指著基礎性的「田野描述」,但它卻需要與現象的反思達到某種內外平衡才行;最後,不「相信自己」就沒法持續性的書寫,但不「懷疑自己」就無法獲致一個質疑批判的空間,以進入第二、第三層……的改寫作業之中。總的說來,這實在是一場無止盡的斟酌和拿捏啊。
據小說家的說法,「作者村上」其實是靠著「跑者村上」的每日磨練,獲致「專注力」和「持續力」這兩項關鍵能力(除了「才華」之外),才能維持其數十年的持續作品發表。叫我驚訝而欽羨的是,「跑者村上」究竟是如何從晨起練跑中領悟到「作者村上」所需要的技藝和能力?「跑步」和「寫作」的關係是什麼?二者間是透過何種管道而得以連結互通?對此,村上是透過「肉體」與「精神」的關係來討論的:
……人的精神,可能是被肉體的特性所左右?或者說,精神特性對肉體的形成能發揮作用?或是精神和肉體彼此密切影響、互相作用呢?我只能說,人可能天生就有一種類似「整體性傾向」,不管自己喜不喜歡,都逃不了。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調整,但無法根本改變。……(村上春樹,2008: 99)

小說家並非哲學家,落入身心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的探問方式並無可厚非。這本《關於跑步 : 我說的其實是……》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做為村上超過三十年的跑步/寫作經驗的整理,一再帶領讀者去體會他所說的人的「整體性傾向」,去抵達一個我稱之為「身體精神性」的領地,一個超越二元對立的第三空間(只是村上未如此進行概念化而已)。透過本文,我也試著以自己的運動經驗來呼應這樣的身體取徑,並透過對「踏實」、「努力」和「徹底」等詞彙賦予身體性意涵,來回答前述提問中的「如何連通」的問題。
踏實走路
「知識」是抽象的,「經驗」則是具體的,那麼「身體之知」是什麼?它恐怕是一種還處在黏附著肉身、依稀能被感知、卻還不易形諸語言的生成流動狀態。
對於腸胃機能不佳又熬夜的我而言,一般說來,冬季冷峻的清晨不會是一天中太舒服的時刻,那主要是來自於長時間平躺後的消化遲滯問題。不過,這半年以來,無論起床時分何等艱辛,我都會勉力把自己帶去一個住家附近的田徑場,就著冷冽空氣,繞行四百公尺跑道,這差不多已是我每日的「啟用儀式」。這個跑道座落在太平洋旁,一側彎道上可見到部分蔚藍的海平線,天氣好時,更有耀眼的日出相伴,另一側彎道則可以遠眺中央山脈,視野好到可瀏覽群峰的層巒疊嶂之勢。山海之間,呼吸浮沈著。
幾乎已固定下來的四十分鐘行走,身體的直立和穩定向前,既有助於腸胃道蠕動,血液循環也使四肢逐漸發熱——「手暖了!」可說是一個指標,儘管這在寒流來時,可需好一段時間才能辦到。慢慢的,我從行走中感受到越來越多的差異,這是過往年輕時的我不太會辨識到的,例如:駝背緊縮的肩頸胸背vs.向上延伸的脊柱與鬆軟下垮的肩膀;雙手插在口袋裡的閉鎖體態vs.雙手和全身在自然的韻律中擺動;微微喘氣的狼狽感vs.鼻息韻律的穩定勻稱。我從來都無法在一開始就達到理想的姿勢,有時身體就是想縮著,沒有理由,就算縮著不一定舒服,也想要堅持這樣,一直到某個時間點之後,內部熱能累積足夠、機能活化之時,我才願意放下那無謂的堅持(但在稍早那可一點都不「無謂」)。當感覺的「引擎」已然備妥,萬事俱全,我就會脫下外套,繼續往前走去。
由於我雙腿「外八」,兩隻布鞋的外側都嚴重磨損,內側則完好如初,可以說是內外極度不平衡。後來我又發現,自己走起路來似乎踏不實、踩不穩,真沒想到我已這樣行走了四十年了。我曾向瑜珈老師請益,老師認為我的情況並不嚴重,可以用意識來調整,讓自己在行走時稍微「內八」,讓足弓內側與腳板其他部位一樣緊密貼地。沒想到,後來我在PU跑道上幾乎可以完美的做到這一點。
打那時起,我開始感受到行走的美妙之處,也體會到一種身體意義上的「踏實」——讓整個腳底穩穩的、平實完整的踩踏於平地上,不再會因腳板未完全的觸地、無法獲得平衡,而需要急忙將另一腳抬起。此外,我也才體認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意義——每一天,都是這樣從零開始,總要經過熱機、運作、儲備能量等一道道工序,經歷一個時刻都在「奠基」的歷程,方得迎來當日的成果。

努力及其餽贈
大約六到八圈操場的距離。身體熱了、呼吸勻了,我會就著一棵林蔭蔽天的榕樹,面對大海做起體操來。大致上我做的項目如下,但多少會有一些微調:兩臂大車輪般前後繞行;頸部360度雙向轉動;肩部聳起落下向前後繞行;手肘和腳踝轉動;扭動腰部;骨盆前後擺;雙手插腰骨盆呈∞字型轉動,最後則是上身的體前彎和後彎。
這些涉及了「旋」或「扭」的轉動,予我極大放鬆效果。由於此時身體已熱,我在扭轉的一鬆一緊之間,便能清晰感受當下極限與拉筋的張力。只要鼻息調整得好(因為有時會忘記呼吸),動作掌握得當,身體會變得更加鬆軟,慢慢的將各種體氣和體液逐一排出:哈欠、鼻涕、眼淚、打嗝、放屁、唾液等,說來有些不可思議,但那確確實實的每日發生著,而清潔後的身體也變得神清氣爽。由於實在並不優雅,故必要選擇一個無人的空曠處來進行。
我的重頭戲是最後一個動作——上身體前彎和後仰。我照著瑜珈老師的提醒,做前彎時先將膝蓋微彎,手指自然觸地後才將膝蓋向後慢慢挺直,此時,大腿前方的股四頭肌要用力、繃緊,小腹要縮,背要放鬆打直,同時去感受小腿後方漸強的張力,直至呈一直線為止,甚至可將膝蓋頂到最底,加強感受的強度。瑜珈講求不可「硬凹」,因此在面對肌肉與腿筋張力時,只能一次次緩緩拉伸,心急的話則容易受傷,我能做的只有讓動作抵達「正位」,然後透過一呼一吸,透過內心,由時間帶著身體自然的「深入」。對這個過程,我實在說不出哪裡需要「努力」,但確實,有「努力」(卻非用力)會獲致不一樣的成果,那包括了:細心的感知(一種照料的心念)、耐心而不怠惰的身體以及專注而平穩的呼吸,但這些都並存於一種整體性的運作之中。
然後則是後仰。後仰講求重心穩定、鬆緊適中和平衡。請想像這個畫面:當頭部整個向後仰,下至某個極限,雙腳就沈穩有力的向下踩入,而平衡點就在此二者之間。這無疑是一個有風險的動作,只要頸椎僵硬、腰部過緊或無法在恐怖平衡中放鬆,都有可能導致受傷。一旦受了傷,我就覺得人生好苦,要付出好幾天無法暢快的扭動身體的代價。那麼,當天能下腰到什麼程度?是頸部向下一點?還是腰椎後仰幅度保守一些?這都要靠著身體給出反餽,我才有調整的依據。此外,如果當天過敏鼻塞,則身體無法完整「吞吐」,會導致整個生命體的舒展變得極為有限。有時,我會在下腰之前先拍打大腿兩側的膽經(風市穴),或是臀部的環跳穴,並揉揉脊柱兩側的膀胱經,都有助於肌肉的鬆弛與動作的流暢。
「前—後」算一次,總共需做四到五次。每次的間隔裡,我會做一些零碎的伸展和調整,但這些小動作是自然發生的,已經跟前頭的固定化程式不一樣了,因為經過四十分鐘的運作下來,身體已會自己「告訴」我,此時是該調整骨盆,或是再把頸椎鬆開,還是肩部再做幾個迴旋——我需要做的,就是跟隨指令即可。
當體氣一一排出,整個人會變得鬆弛、疲倦而酣暢。此時身體又「說」了:它已經熱了,它完全「上膛」了,它感謝我所付出的努力,也餽贈我以暢快淋漓的感受。透過升起的朝陽,它對我昭示:「可以開始這一天了。」
徹底鬆開,張羅所需
交代完動作後,現在可以進入較細微的體會:身體向後之際,後背與腰際的(先是)微痠與(後是)極度伸展,會帶來緊張後的大大鬆弛;而在前彎起身、逐步向後的過程中,脊椎骨一節一節從蜷縮到伸展[2]、血液則直衝腦門,鼻息全通,會給予我無比清醒的感受。待身體回正,一切下落,此刻只能以「神清氣爽、通體舒暢」來形容,那顯然已是不一樣的身體境界。
不過,此前五十分鐘的身體運作的「徹底」程度,在在影響著此時所能達到的境界。至於今日「是否徹底」,則是透過先前身體曾創造出的「差異值」來「知道」的。剛開始時,我可能連向前下腰都有困難,直到某一天,我突然不只能將膝蓋徹底打直、感受後腿的張力,還能在拉伸的調息中體會後腳筋的張馳感。原來,人的領悟是在努力後以全然的被動性來領受的,唯有身體曾給過我們一種絕對的差異後,我們才會在日後的某個受傷、偷墮或不太努力的早晨,體會到今日的自己何以「不夠徹底」。
然而,「徹底」談何容易?每日都有當下的氣溫、鼻子的暢通度、肌肉的緊張度、行走擺手時的流暢度,甚至連步行中的骨盆擺動幅度和腰間鬆弛程度都是不同的,方寸之間,需要覺察和調整,而第一圈的走法/呼吸法和第五圈的走法/呼吸法,也是完全不同的,甚至,要不要趁勢跑起來,給自己較火熱的身體感,都是一個選項。於是,我只能透過包含了動覺(kinesthetic sensations)、感知(perceptions)和感覺(feelings)在內的綜合性覺察(awareness),不斷主動去運作身體並時時微調之,付出時間和耐心,又不能過度用力或急切。沒有這些,我無法抵達那份「透徹」。那麼,所謂的「透徹」不就是融合了時間、被動、耐心、覺察、靈巧、勤奮、技巧和適時轉換等多元要素於其中嗎?
雖說這一切全得靠「日積月累的努力」大抵是正確的,但這樣的說法卻會帶給人一種過度線性的錯覺,而事實遠非如此。原因在於,每一個明天所需要面對的,並非是前一天運動完那一刻的身體境界,直接從那裡接續努力下去就好;相反的,每日清晨起點的身體,是承受了前一天整天操勞、飲食、心事、或許又還加上睡眠不足的狀況,當情況更糟一些,要面對的就是「不堪的身體」了。
但無論如何,每天早上,我一來得放下昨日的一切,二來得承接那做為「起點」的當下身體,透過努力來進入另一個世界,才能獲得全然的休息以及再出發的動力。我不一定都能成功,事實上常常已經到該上班的時候了,效果依然有限。然而,我在主觀上卻覺得此事越來越不吃力,且已然有了更高的意願去執行它們,我想,是因為那曾經的差異感受,使它們不只是枯燥、遲滯的機械性動作而已。某程度上,在這個由「行」、「扭」和「轉」和「呼吸」所構成的動覺空間中,在我內裡生產出一個「差異他者」,一種透過身體和意志努力可能獲致的生機感,一種融主動性與被動性於其中的流變狀態。
一個(從事助人工作的)朋友曾提出一個說法:面對那些處境較邊緣的弱勢族群,助人者應該當一位好的「張羅師」,恰如其分的為他打點出某種「照顧的格局」來。他所使用的「張羅」二字其實含義甚廣,包括「照料處理」、「籌劃」、「安頓」、「照應」、「接待」、「張網」、「搜捕」等意涵在內(無作者,無日期),與英文中的”care”(照顧、照料)相近,都是指:人在面對某一「對象」(人、事、物)時,透過某種程序性的安排或創意巧思,開創出一個得以關注的空間,以成就該對象的美與善。
與此類似,在我的運動案例中,能否抵達所謂的「徹底」都取決於一種「張羅」自己身體的能力,這聽起來或許稍嫌怪異,但我們只要看運動員的例子便可明瞭:每個優秀的運動員都有打理自己身體的能力,他知道如何在即將到來的大賽之前,一步一步加強練習強度,適當時貪懶一下,以稍微欺瞞身體、以博取其繼續賣命服務的甘願,之後,則在另一時刻將「油門踩到最底」,使肌肉骨骼習慣正式比賽強度,並達到一種機械下意識反應的運作狀態。所謂的「張羅」,就是透過一種差異的細緻分辨,以及某種合理的調整鍛鍊,來幫助自己全身心的投入於某種身體運作的動勢裡頭。

跑者與作者
本文透過對運動經驗的思索,呼應村上春樹所開拓的這條「身體精神性」的探究路徑。無論是「踏實」、「努力」或「徹底」,都是一個介於肉身運作、身體感與知性掌握之間的身體之知。然而,村上馬上會說,不只是如此,他馬上會將話鋒轉到小說,進一步去談寫作做為一種超越生物有機體層次的「身體作業」,一種肉眼不可見的「肉體勞動」。而更重要的是,是跑步在教會他如何應對這種長時間、重量級挑戰。
寫長篇小說的作業,我認為根本就是肉體勞動。寫文章本身或許屬於頭腦的勞動。但是要寫完一本完整的書,不如說更接近肉體勞動。……坐在書桌前面,精神集中在雷射光的一點之上,從虛無的地平線上升起想像力,生出故事,一一選出正確的用語,所有的流勢全部保持在該有的位置上——這樣的作業。比一般所想像的需要更大的能量,且必須長期持續。身體雖然沒有實際移動,但那剝削著骨肉般的勞動卻在體內不斷地動態進行。……這種作業對作家來說,要求使出渾身解數的肉體能力——往往到殘酷役使的地步(村上春樹 2008: 94)。
村上透過跑步來領略一種生命的吞吐調配之道,而這個經驗不會只是他寫作活動的隱喻(metaphor)而已,實際上,村上是憑藉著同一副身軀,以其曾經抵達過的(或在身體裡不斷量測著的)幅度、深度、廣度和柔韌度,來應對著書寫長篇小說的每一關卡。這當中,肉身本體層次的差異生產與感知的細緻化顯得極為關鍵,「差異」使人常保生機,不致落入寫不出東西的死胡同,而「感知細緻化」則讓人獲得一種賦予各類困境以某種「理路」的能力,進而得以去步步張羅自身所需要的一切。這一切,全都默默的鎖在我們的身體裡,一個我們僅略知一二的身體,仍有待深掘的身體。
如同上一篇〈身體—物質的精神生產(之一):哀傷之身及其流變〉所談到的,身體做為主體與世界的連通管道,總能將我們帶向一種「非知之知」,而這樣的「知」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肉身主體全然中介了我們「面向世界」一事,它既可以帶我們走向世界不同角落,或將無盡的悲傷全然禁錮軀體之中,也可以帶我們進入一個「寫作的身體」,成就那胸豁之間的大山與大海。
註腳
[1] 本文的上篇是〈身體—物質的精神生產(之一):哀傷之身及其流變〉,理論上本篇應該要取名為〈身體—物質的精神生產(下):論「踏實」與「徹底」〉,畢竟兩篇的確分享著同一個想法——身體做為連通管道橋接了主體與外部世界,並進行精神性的生產。然而,後來我認為「身體的差異生產:論踏實、努力與徹底」更能表達本文意旨,因為如同後文所述,透過運動的差異感受和身體的微調的連動運作下,身體將對「運動中的主體」生產出了一個主體的對象(更準確的說是上一篇所提及之Hermann Schmitz所謂的「半物」概念),使主體對它持續的發展更細微感知並繼續付出努力,而且,它們已經上升到了一個近乎「概念」的層次,指向「踏實」、「努力」和「徹底」等語詞的身體性意義。
[2] 附帶說明,上半身往前折曲的程度會影響後仰動作中脊椎的延展幅度,這非常有趣,這種推進是一波接著一波的,沒有前者的努力不會有後者的成效。因此,脊椎骨之間是開始較為鬆脫、給出了相互空間,抑或仍有兩三節骨頭還黏在一起,我也體會那細微差別。此外,過往我曾羨慕學游泳的女兒能在水中「蝶泳」,我幾乎無法感受那種有如海豚魚兒般、如此靈動的身體運作方式,但當我不只能前後彎伸,甚至還在腦中升起一種「鞭子」的意象(即整條脊椎骨的前端(上接頭骨)和末端(尾椎)猶如鞭子一般甩開來的波動感與張馳感受)之後,這個全新的身體經驗彷彿為我開啟另一個通道,我因而也開始可以跟女兒討論她蝶泳時的身體狀態了。
參考文獻
賴明珠(譯)(2008)。《關於跑步 : 我說的其實是……》。臺北市:時報文化。(村上春樹,2007)
無作者(無年代)〈百度百科—「張羅」〉。2024/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