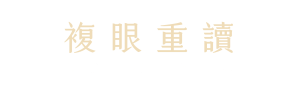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王鏡玲(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本篇文章初稿發表於2021年東海大學「靈異經驗與哲學反思」工作坊(2021.12.17)
前言—被邊緣化的「我們」神話劇
個人在生活中遇到苦難或考驗的時候,往往是發現自身的有限性、對自我探索的開始,發現「我」原來不只是那個原先的「我」。這種探索如果和人之外的宗教信仰文化有關,就會進入「我」如何和神聖的「他者」或是神聖的「我們」–精神、神靈、靈魂、自我、生死、靈性…等等信仰文化上核心的理念產生關連。「神聖」(the sacred)是人渴望「溝通」的需求狀態,而當宗教經驗被制度化之後,就從人與神聖溝通時原初個體化的各種流動、不確定的特殊性狀態,進入被訂出各制度化、集體善惡的價值判斷[1]。
不過,個人面對痛苦時的自我探索,往往是個別化的事件。這種焦慮不安、不確定感,甚至面對死亡的恐懼,來自生命實況的個別化事件,並非集體週期性的神聖時空感,而是個人在面對種種挫折考驗的深淵中,重新找尋解決的機會。因此,個別化的信仰探索,和透過以廟會慶典的集體顯聖儀式,來尋找生命動力的方式有所差別。
現代科學宣稱下,人是一個獨立自主,擁有理性,去創造人所屬的現實世界,但現代科學卻難以提出人的理性,可以對於去感應人與人之外的靈魂、精神、意志的能力提出證明[2]。每一個生命與另一生命之間隔著一道鴻溝,這是獨立自主的人的孤獨感。但人也能意識到自己並非孤島,並非現代工業社會疏離的一座孤島,人一方面想逃避和跳脫過去傳統世界觀裡,曾經遵從的宗教信仰權威、家族關係所塑造的自己,另一方面又面臨當前疏離的社會關係中,人必須蛻變,重新去找到屬於這個時代自己的生命主體,與其他主體之間的溝通方式。
這個新時代生命主體或者有自己的中心,或者虛無漂泊、隨波逐流、隨遇而安。個別的生命主體不再只是被動、被洗腦的僵化個體,而是能夠在介於主動與被動之中的自我追尋過程,逐漸覺知、參與在從過去-現在-未來的共同體,體驗變化生成的悲喜聚散歷程,讓自己好像經歷了和自己相關的古老DNA基因關聯,或者信仰或價值觀共同體的前輩曾經歷過的生命流變,從當中看到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關連性,以及自己被賦予的或多或少的任務,或者價值[3]。
雖然以下我要探討的通靈現象,在靈性探索上往往被這些通靈者所相信的「冤親債主」、「因果報應」、各種靈源受苦受難…等等負面、仇恨、反動力的價值觀所綑綁。但卻也是個人面對自我「陰影」、怨恨、報復,重新追尋「我是誰」的開始[4],「通靈」作為一種個體「成為……」的變化生成,變成另種「自我」宛如「他者」的生命狀態或角色扮演。透過這樣的個體去成為另一個「自我」宛如「他者」的變化生成,讓我們重新看待現代社會以及學校教育,尚未好好正視的面對生死流變的問題。
我們從這些通靈現象一方面去理解通靈者和過往死去多次的「我」(被解釋為「累世」的輪迴)或「他者」的靈魂溯源、通靈者的血緣(祖源)所面臨的缺憾,與通靈者靈性相關的眾多生命體(被解釋為「冤親債主」)之間,那些看似反動、負面,或是心理分析上討論的「陰影」的考驗[5]。另一方面我們也從這些天地、乾坤、神佛、能量…等等,古老神話元素的能動力,發現在祂們尚未被權威化,變成控制人的道德規範與箝制之前,可以個別化的意義流動性。
此外,這當中也讓我發現通靈者現實人生的慾望糾葛的催逼,而讓通靈者不得不去尋求扭轉困境的歷程,如何面對考驗,找到解決之道。這些也揭示了在現代台灣跨地域性與去地域性的多元宗教信仰現況的變化,個人化的通靈方式,變成另一種面對工業社會、面對政治強權的逃逸路線[6]。
在我之前的通靈研究中,就發現這些個人的超自然感應,意味著人對於人自身實況各種衝突、限制、接納或創造力。這也包含仍然受父權社會文化影響下的一般生理女性,如何透過感應到「神聖」,讓她們在處身工業社會變遷中,在傳統與新時代女性角色之間,在她們的階級、世代的角色扮演,在面臨人生考驗時,如何從當代的通靈信仰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中,跳脫原先現實身分,進入「神話劇」角色的扮演,從其中去找到企圖翻轉人生的可能性。但是,她們所使用的「神話劇」中神聖權威的意識形態或價值觀,也再度限制了她們對於主體能動力的發展性[7]。
以下我將以台灣新興泛民間信仰「通靈」現象中,以通靈者「開靈文」為主的圖像書寫與通靈「神話劇」的關聯,來探討台灣當代庶民與藝術表現的生命美學。原先被視為後援者、助手的一般人,如何在稍縱即逝的個人生命史中,在不斷重複發生、卻也稍縱即逝的神話劇中,找到屬於「我+們」的神話劇。在通靈的變化生成、稍縱即逝的狀態下,成為自身神話劇中的主角,獨當一面、擔任救援任務,去救度受苦靈魂。
一、「通靈」體驗的外在性與內在性[8]
「通靈」體驗範圍廣泛,從古老希臘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的神話祭儀[9]、基督宗教《新約聖經‧使徒行傳》裡的聖靈充滿[10]、《山海經‧大荒西經》裡通天的巫群[11],到現代新興宗教的靈性復興運動[12]、基督宗教的靈恩運動[13]、以及台灣當代的靈乩風潮[14]等等……,都是可以關連的宗教現象歷史光譜。在本文中是指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與自身所感應的神聖力量之間的互動。面對宗教現象相當核心的通靈體驗,如何詮釋就構成不同研究派門的特色。我選擇用「通靈」的字詞,而不使用「神秘主義」/「密(冥)契主義」(mysticism)[15]、漢語的「巫」,或「薩滿信仰」(Shamanism)等等字詞,這些字詞背後,都有其原先宗教傳統的特殊性,和台灣民間通靈現象之間有關連,但不等同。「通」具有宗教人「去感通…」、傳達、通曉、以及雙向往來、溝通交換之意,不同於從「神聖」界的角度,去詮釋如何透過人、事、時、地、物來展現的「顯聖」[16]。不同的族群、階級、性別、世代,在強弱勢文化體系的衝突鬥爭中,在時空演變過程裡,不斷找尋個人與相關的信仰團體之間,對於「聖界」的系譜與版圖。
台灣漢人宗教的神靈世界,不斷融合拼裝從古到今傳統儒、釋、道、巫的權力階序(hierarchy)的神譜,再加入自從一九八零年代後引進的各種新時代運動(New Age Movement)風潮的新靈性類別,隨著時代變化,不斷擴充改造各種宇宙生成的氣化或能量派門,構成多元並蓄的靈性探索領域[17]
「通靈」現象在本文是指主體感通到與自身更內在的「我」,或是更超越的「能量場」(我們或者「他者」),可因其所感通的內容,而稱為「能量體」,可以以人格意志的「他者」能量場現身,或是以非人格的「他界」能量形式現身。並因為感應到這樣的能量場,而讓宗教人在面對生命困境、挑戰或考驗時,具有承擔的意志力,企圖活出有別於原先的生存狀態。透過肉體的感官知覺與行動表現,以及個體與其所處身的共同體之間的認同關係,來作為「通靈」的外顯現象。
通靈者的聖界包含神佛的世界、祖源的世界、以及其他的靈界(或者被命名為有情眾生、孤魂野鬼、冤親債主、非人類的動物靈、植物靈…等等)。在多神信仰系譜裡,按照儀式目的而有不同聖界的協助。除了聖界「多元」的信仰體系混搭的特質之外,還包括人與所感應的「靈」之間關係的「個別化」[18]。過去被以男性宗教祭司(道士、法師、童乩)所主導、以制度性的儀式來祭拜聖界的漢人信仰文化,在最近的台灣會靈山系通靈信仰,則出現強調通靈者「個別化」與聖界關係,以及母性神占重要主神地位的靈力表現,也成為通靈現象趨勢。通靈不再是一種先天體質的論述,每個人都可以藉由任何一套漢文化混搭的修煉傳統之汲取,經由後天的培養,而獲得通靈的能力[19]。
諾伊曼(Erich Neumann)曾指出在心理學上,個體所感受到這種動力是強迫性的[20],正如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所言的,神聖顯現自身,讓宗教人感應到這樣的動能[21]。「靈」不只是他界,而是透過「我」的主體去感應,「通靈」包含外在性與內在性。首先就外在性而言,對於顯聖形式與靈力運作的象徵系統,反映了當今物質世界雖已深受現代西化文明所影響,但是神靈世界仍以華人帝王權力階層的運作模式為主。通靈者一方面藉由「神聖」和現實世界的距離感,來凸顯人對於古老、崇高、難以測度的「外在性」的敬畏與崇拜。另一方面,通靈者經由「神聖」所賦予的自我肯定與權力意志,透過可見與不可見的儀式象徵交換—靈力展現、供品祭拜、符令、「開文」與金紙的燒化等[22],來企圖化解苦難來源的威脅,讓無力改變現狀的個人,找到暫時的寄託。
其次就「通靈」的內在性而言,透過喚起對被壓抑、被遺忘的內在自我的探索,讓個人得以挖掘更深的自我潛意識,得以重新面對眼前難以承擔的身心考驗。這裡牽涉到的是,這些通靈者對於「累世」、「輪迴」、「因果報應」等信念的信仰,以及通靈者自身的「靈源」在「累世」輪迴中,所承擔的任務完成與否、和其他「靈源」/「冤親債主」之間如何解冤釋結…等等個人神話劇版本的一再演繹。通靈者透過自我與內在靈性的覺知,以及外顯的身體律動的顯聖角色扮演,傳達難以言喻的冥思與想像,並合理化通靈角色與個人現實命運的關連[23]。雖是現實人生平凡的通靈者,藉由意識到累世輪迴中曾經生為帝王將相貴族、曾經梟雄亂賊,來對照與補償此生坎坷崎嶇的缺憾。
二、身體不只是身體—反映自我處境的靈動展演
在現今台灣快速現代西化的工業社會裡,許多血緣與地緣共同體的人際關係,已經產生很大的變化,尤其從台灣各地移居到大都會的異鄉人對自我處境的定位。儘管異鄉人依然交織著殘存農業社會的慣俗傳統與物質文化,血緣或地緣共同體的認同,但越來越多都市生存考驗以及遭遇現實的不順遂,讓他們求助的信仰對象,也因為新的人際網絡,出現新的神聖救援團隊,來解決生活中的各種不確定性的問題,以及面對各種心理壓力的調適[24]。
這些通靈者的「身體展演」不像操五寶、必須肉體見血、把自我意識暫時讓渡的童乩形象;也不像傳統陣頭有一定的儀式結構、團體陣勢、禁忌、肢體身段與服裝法器等神將既有特質。通靈者靈動時的穿著,除非有舉行特別的團體儀式,例如去各地會靈進香,其實很日常。透過這些出現在我日常生活中親友與其友人,甚至牽涉到我個人(詳見下文),他們讓我有機會參與到通靈者的「開文」與神話劇,讓我發現原來就在日常處境之中的民間文化靈性光譜,並非要去到他鄉異地、有明顯城鄉差距的地方訪查。這是「我們」的體驗,而不是「他們」的個案資料。他們讓我意識到面對人生的考驗下,所激發的庶民稍縱即逝的宗教美學,與奠基於切身需要的自我探索。
這些通靈者因為各自被揀選的個人神話情節,例如在自己夢啟、以及被資深通靈者告知被神明揀選,以及遭遇重大生死病痛考驗,讓這些剛入門靈動者有了「靈知」,亦即,感應到神聖力量和自身所面臨的現實考驗之間的因果關係。這些神話劇情透過身體靈動展演所顯示的意義,從一開始的混沌不明,不斷地在資深通靈者引導下,學習加以辨識,成為可以自我解讀的各種神話劇系列。尤其包含了靈動者在其信仰體系對於「累世」、「輪迴」、「因果報應」、「冤親債主」等等信念,所展開的溯源,以及關聯到現在、未來的神話劇情。
這些神話故事以通靈者「第一人稱」的遭遇為核心展開,像一齣又一齣連續或不連續的劇情元素,進入想像與幻境的時空之流,和現實人生的際遇穿梭交織,我稱這為通靈者的「神話劇」符號系列。進入自身「神話劇」的通靈符號系列,那些神話元素包含了恩怨愛憎的慾望、圖像符號的書寫、口語吟唱或傳講宗教語言、自身以及與其他通靈者之間的感官與肢體動作展演…等等一連串的通靈體驗。這些身體展演的現象,大部分以台灣在地民間文化象徵體系為主,例如古裝歌仔戲的唱腔和身段、或是民族舞蹈、武術的肢體動作。通靈者開文所書寫的圖像也從類似自由聯想的塗鴉,到具有古老漢文化宗教象徵的線條、構圖與色彩[25]。

當這些人進入通靈的「神話劇」時,不同於一般日常的時空感[26],跳脫現實社會角色的身份,進入另一齣「累世」某個神話時空的角色設定。這種轉換性讓個人原本的社會角色,有了新的流動性,例如我在之前的研究,提到的一位中年女性變成一位嘻皮笑臉的小頑童,被視為玉皇上帝的小孩。或是一位中年男子變成一隻做出像猿猴的動作,被視為累世曾經降生為動物,在探索自己的靈源時,「動物靈」被召喚出來。當通靈者過去的「靈」源被召喚出來時,他們暫時跳脫現實社會角色,生理性別區分、社會階級高低、物種特性(人/非人/動物),「自我」宛如成為「他者」,有了新的性別化、物種化的可能性,在他們所隸屬的信仰團體的神話劇本與角色扮演的共識下,形成暫時性的身份跳脫[27]。

作為日常生活中勞動者的身體,在通靈儀式的展演過程中,身體暫時不屬於勞動的身體,而是轉換為從初入門時的混沌不明的肢體擺動,然後進入武術、舞蹈、神話劇的肢體語言[28]、或遊戲般的身體。這些讓通靈者暫時跳脫了謀生勞動的社會化身體,在通靈的訓練過程中,通靈者以「神聖之名」,讓肉身從勞動或現實條件下的實用價值,轉向與切身禍福攸關,又展現出宗教、藝術、遊戲的精神性交換價值的追求[29]。
尤其女通靈者,透過進入聖界儀式所展現的自我價值,來讓她們找到返回世俗的男性主導的社會之後,面對或逃避困境與挑戰的因應之道。這種精神性想像,因為依賴神聖「他者」後,而產生安全感與自尊;但也因為神聖「他者」所產生的權威管控,而感到被支配、甚至被壓迫的拒斥感[30]。更多的是,因為被告知「冤親債主」的因果報應信仰觀,讓他們承擔很大的精神與肉體上的壓力,必須找尋將這些陰暗面、反作用力加以轉化,找到自我肯定的正面價值[31]。不過,透過人對於超自然的想像與體驗,台灣民間靈性信仰的探索,看似現實取向、利益交換、充滿自我中心的權力慾望,卻又表現出對抗挫敗與災難、對抗不確定命運的生命動力[32]。
這些通靈者的圖像書寫與肢體歌舞,不斷在他們個人靈修和信仰團體儀式中重複發生,但又稍縱即逝。因為面對的是個人迫切的現實考驗,往往處理問題勝過於拍照錄影紀錄。尤其面對痛苦,往往避之唯恐不及,並不希望被留下畫面,透過儀式的化解,消失於無形。尤其是必須燒化的開文,這些燒化的步驟,除了轉化有形到無形的象徵意涵之外,也意味著斷裂、拋棄負能量狀態的改變[33]。不過,最近開始因為拍照錄影越來越方便,而有更多能見度。只是,他們所繪製的圖像符號,往往必須燒化,來和無形界溝通,很少留下探索的圖像或文字符號紀錄。

在榮格(C.G. Jung)探討心理與圖像的研究中,他發現圖像所顯示不斷重複的一些特徵,和我以下要探討的開文也有所呼應。這些特徵包含:混亂中的多重性與秩序、二重性、光明與黑暗、上下、左右之間的對立,旋轉、對稱、放射狀……等等造型上的動力形式。古老心靈的動力,透過這些開文,一方面顯示了開文者所面對的具體現實,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從具體的個人,到集體無意識之間的連結,透過身體的感官展示,就是最好的動力場[34]。
這也是杉浦康平所提出的,這些光明與黑暗、上下、左右之間的對立,旋轉、對稱、放射狀…等等造型,不只是停留在個人的人生體驗上,而是與更古老的血緣、DNA生命記憶有所連結[35]。透過造型的感受,喚起我們尚未覺知的感官與悟性,感受到古往今來對造型的意義互相之間的照應。杉浦康平認為,「靈」(ち)是體內循環、自然界氣息與天地之間的靈力、信仰上的咒術魔力…等等,在「靈」的作用下,「形」變成有血有肉的「型」,產生蓬勃生機的搏動[36]。這些圖像造型都是從古到今,被數不清的無名藝術家不斷珍惜、守護、轉化,成為今日我們所共同擁有的宇宙生命記憶的圖像[37]。
即使是以下所看到的只是稍縱即逝、根本沒機會留下的通靈者某一生命剎那、或大或小遭遇中的「開文」圖象暫留,這些圖像就像是古老神話大敘事、古老圖像資料庫中隱藏的一個個小檔案被叫出來一般。這些個人所書寫的圖像和神話劇的敘事或展演,無須返回到有固定標準的原始神話版本,而是隨著新興宗教不斷混搭交織的神聖世界,產生以通靈者個人現實遭遇為中心的神話小故事,以及我所稱之為的神話劇。這裡用「小」故事是來對比過去那些傳統流傳的神話大敘事結構。
三、暗藏現實心境的庶民靈性美學行動
「開靈文」或簡稱「開文」現象,是相當值得探討的庶民靈性書寫行動。這種透過身體感受、個別化的需求、神聖感應的神話劇情、視覺圖像的書寫,在線條、構圖布局與典型的宗教色彩配置下,反映出通靈者對照現實生活的庶民美學行動。
請容我先講一個和我個人相關的第一次看開文的初體驗。大約是十多年前左右,有一次我回彰化老家,拿衣服去附近無底廟旁修改時,修改的中年女裁縫師,正在寬大的裁縫桌上低頭畫圖,原以為是畫衣服樣式,但驚鴻一瞥,卻發現,對開尺寸左右的淺藍色底紙上,充滿暗色線條,非常繁複,彷彿洪通式的構圖風格。還來不及看清楚,裁縫師趕緊收起來。當我表明宗教系教師的身分,詢問是否可以拍照當作教材時,她拒絕,但告知下午我來衣服時,會請前輩過來說明。
下午去拿衣服時,她請來一位年約六十的師姐,穿著唐裝,可能是她的引導者。師姐告訴我,那種開文一旦被拍照,就無法完成開文燒化給過世者的儀式。因為我表明用意,並非有敵意的挑釁者,只是想做上課教材,讓學生知道那是什麼。於是那位師姐請裁縫師另用黃紙開一張文給我,裁縫師連打數個嗝之後,用紅筆當場開一張很整齊的文給我。當時,我頗為尷尬,一方面受寵若驚,可能對方藉由神聖力量來宣示另一種「靈知」的權威。之前沒有遇過被神佛現場降乩開示,當時我有種被迫遇到不可知的陌生權威、必須敬畏尊重。裁縫師表示並不知那張畫給我的開文之意,透過一旁的資深師姐來說明,告知內容是對像我這般傳道授業者的勉勵,並讓我帶回,可以給人看,不用燒化。那是第一次遇到有通靈者的開文,是專為我所寫的,所開的「文」那張紙本,還可以保留下來。

這張圖對我是一種奧秘,也是一種提醒,在不斷重複中有變化的對稱、螺旋線條。這是很簡單的構圖,可能對很多開文者相當熟悉,但對我卻相當陌生。一開始我甚至對這些看似單調的線條,感到有點不解,彷彿看到被制約、機械般的書寫,像小孩子被迫寫作業。當時還有點小失望。但是當我再度凝視這張超過十年以上的圖像時,我的看法逐漸轉變。跳脫具體的「開文」在信仰上的功能–做為人師的勉勵之後,在凝視時,我感覺有一種古老力量出現了。那是回到書寫符號的原初,在人與人、事、物、慾望..等等,尚未被命名,那種難以言喻的對稱、旋轉、重複、分合等,簡單造型的符號奧秘。
這當中帶有不斷主動或被動的重複交流,重複去認識自身在書寫時為何要發出重複訊息的探尋。堅持什麼?又想要變化什麼?線條與布局的單純,代表一種想要突破與堅持的張力。這裡包含兩位通靈者在「靈知」上的合作,面對我這個被她們視為強勢文化資本的知識階層,所提出的靈力權威展現。有意思的是,這張文並沒有蓋印,沒有署名,沒有日期,好像是像我示範如何開文的動作,並不像以下要探討的開文,這是一張沒有開文者署名的開文。
正因為沒有燒化,就變成一種意外的提醒,但反觀如果是充滿痛苦慾念的開文,那麼燒化反而是另一種銷毀的釋放。或許,問題不在是去了解某個符號意味著什麼,而是去了解它指向哪些其他的符號,哪些其他的符號和它連結之後,形成了怎樣的意義網絡[38]。
「開文」對通靈者而言,既是自我理解與集體修行精進的方式,也具有溝通「他界」的功能,更具有紓壓、發洩、催眠一般進入潛意識或無意識的功能。通靈者的「開文」,透過默想、靈動與書寫,以及「開文」之後自我解讀,或請資深通靈者解讀後,搭配相關儀式燒化完成每一次的「開文」過程。藉著不斷「開文」的視覺化書寫,以及開文當下的心理感受、身體感官變化,讓通靈者既面對那時所遭遇的現實處境,尋求聖界的互動,完成靈性的階段性自我修練。在所開之文透過神佛見證下,完成燒化儀式,得以向所祈求的「聖界」推薦、求赦、救度自身或「他者」(在世或已逝親友、祖源、其他需救度的「靈」),並不斷精進自己靈性修練。[39]
按照一般通靈者對「開文」介紹,靈文可分為天、地、人三種、而人文又稱為水文、書寫時又以三種顏色為主:紅色(天)、黑色(地)、藍色(水)、此三種靈文各有其使用之處,一般信眾可以自己的行文方式來書寫。開文做為祝禱、解冤、消災之用,和疏文、懺文功能相當。「天文」用於某事欲稟奏上蒼或祝壽、祝禱及請求神佛協助等,多數以黃紙、紅字書寫。 地文:用於排解冤親惡業、祖先(祖源)及與冥靈(鬼)、溝通上疏或切結證明使用,使用時可以紅紙黑字或黃紙黑字為之。水文:用於消災解厄、如人生在世總有不順遂之時[40]。我以下想要探討的是如何透過「第一人稱」通靈者所展現的有「神話劇」劇情的開文,和個人生命處境的探索,會以黃紙紅字的開文為主。
以下我想先從一個靈性信仰團體的儀式現象,來探討通靈者的開文與神話劇,作在集體性儀式的意義,再進入屬於個別化通靈者的開文意義探索。
四、海邊普化儀式與開文[41]
在我之前海邊普化的研究裡,曾探討參加全台一年內五方海域普化儀式的主事者,在普化儀式前一年年底時,就曾夢見自己在「開文」,在一張紙上畫「十」字,有四個邊,她一直在那四邊的邊處寫東西。那段普化準備期間,另外一位她所屬的聖德宮的中年男性師兄,也夢到要去做普化,要做多少艘法船,就負責製作法船的工作。他們感應到神明指示有天災,去做普化可以降低與轉化無形靈界的怨氣與痛苦,災難就會降低,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是屬於個人與信仰團體所共同演出的神話劇,「開文」在這些普化儀式過程,具有祈福稟告與消災解厄,協助救援無形界的功能[42]。
「開靈文」具有個體化的特色。寫的時候有時身體會不舒服、疼痛,心情上有時痛苦、沈重、淚流不止。過往累世所承受的痛苦,透過開文者書寫,一方面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也彷彿想像、發洩與釋放與自我治療;一方面祈求無形的「他者」解脫痛苦,另一方面也為開文者自身洗滌、懺悔、或分擔「他者」之痛。信徒個人的生活種種表現運途、身體狀況、家人喜怒哀樂等等,也會在開這些靈文過程中,從圖像或符號顯示出來。但開靈文可能同時兼具給神佛、祖源或靈界(冤親債主或眾生)。每個人都可以「開文」,但寫的人不見得可以解讀意涵,具有解讀職司的通靈者就具備「開文」和「解文」的能力。
就普化的儀式而言,意味著當次擔任普化者所擔任的職責,也具有稟告廟方主神、當地與神明與協助法船皈修神明的用意。所開的天/地/人文開完後,在普化儀式之前幾天,送至主辦普化的聖德宮,經宮主一一看過,搏杯經觀音菩薩見證後,一起蓋上該宮壇的印章後放入法船,當天燒化。普化儀式前的「開文」包含要送往何方宮廟皈修,並說服這些靈界,看看哪一處的神明接納祂們,讓祂們有解脫與提升的機會。

另一方面,海邊普化的開文、也包含通靈者感應到的自身與信仰團隊成員共同的「神話劇」,他們相信這些普化的無形界要送往哪一間宮廟、跟隨哪位神佛皈修。他們透過普化儀式,讓祖靈和無形眾生藉由普化所提供的祭品與紙錢,而獲得療癒與補償,放下對人間的怨恨與作祟,並改善處境,看看哪一處的神明願意接納他們,讓他們尋求自我解脫、提升的機會。海邊普化的儀式所提供的神話劇情,是更具體的協助皈修的目的地,不管是自己家族的祖源、累世冤親債主、曾遭通靈者傷害的生命,例如所殺害及食噉之一切眾生界內之動物、水族、昆蟲、鳥禽類等眾生,以及其他前來現場有待救度的靈界。
藉由通靈者個人透過與「現在」因果關係共構的神話劇,舉辦海邊普化儀式,祈求解開過往以來通靈者與無形界受苦的包袱,這種重返到個人神話劇的詮釋,往往透過集體儀式性的象徵轉化,來讓個人得以在想像與神話幻見中,面對負債與承擔缺憾。透過這樣出錢出力,來救度過往受苦靈魂的儀式,讓這群在現實社會可能默默無名、還被生活挫折所苦的一般人,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卸除個人與冤親債主之間的虧欠,也完成救度神話劇的任務,守護這個島嶼。
這些通靈神話劇的核心關切–「福」與「禍」,其背後往往被因果關係所主導,這些因果都和「超自然」有關係。在相信靈魂不滅、累世輪迴的信仰裡,過去累世曾經對不起的對象,現在(或是未來)必須償還,這是公平原則。但人並沒有因此就變成冤親債主的奴隸或囚犯一般,反而人總是設法和這些「負能量」之間取得妥協、取得平衡。這些「負能量」不只是「負能量」,往往都包含通靈者在現實的挫敗,以及過去以來無法跳脫的內在陰暗面投射[43]。
五、靈動者開文初體驗:自由聯想
經友人介紹,我參與了兩位三十多歲上班族女性小均(化名)和小琳(化名)的認主儀式,以及認主儀式後她們第一次「開文」。這兩位年輕女性住在新北市,到這間新北市宮壇尋求修行訓練之前,就已經常常感受到有「無形」的干擾。
這間我曾去做過會靈進香紀錄的宮壇,主持該宮壇的T師姐,對信徒的修行訓練裡,要成為乩身或成為和神明有「契子女」關係的修行者,一開始就是「認主」儀式,就是在神佛見證協助下,以搏金紙多少的方式,和先和累世的「冤親債主」進行一場「大和解」,一方面確認所要跟隨修行的「無形」師,另一方面透過「開文」和化金紙,來消除和累世「冤親債主」之間的恩怨,才能擺脫祂們報復、扯後腿,真正進入「修」的身份[44]。
小均和小琳按照T師姐指示,貌似謙卑又像玩遊戲般地上香。一次插36支香,濃濃香燻讓他們眼睛快睜不開,呼吸也因被香燻而咳嗽,她們按指示三跪九叩,行禮如儀[45]。這種傳統儀式讓這兩位新時代年輕人,似乎遇到異文化,好像在玩角色扮演遊戲一般,感到新奇。
T師姐以金紙為兩位認主者淨身蓋印後,這些正經嚴肅的儀式動作,讓小均和小琳逐漸靜下心,T師姐告知,將以第一次開文來作為和冤親債主「和解」。開文時用的是八開大小的黃紙,桌上擺了紅色及黑色的簽字筆,主持的T師姐要大家心靜站著,隨著自己的意念在紙上作畫。我看到小均和小琳都閉眼,似乎恍惚狀態,其中小琳手好像開始動了。小琳在設計相關公司上班,有美術的專業訓練,她一開始沒多久,就開始畫出類似自由聯想、遊戲般的線條,但放棄了她原先專業美術訓練的構圖,放鬆自己。兩位都閉眼,小琳一邊畫一邊笑,旁觀的人都不了解她為何發笑。我在一旁觀看,覺得若不和剛剛帶有神聖權威的儀式相連,就像是一種自由聯想的塗鴉遊戲,我個人也會做這樣的隨興塗鴉。

但是T師姐看到小琳邊畫邊笑,就開始說出了她感應到的小琳「神話劇」。她說小琳本是天上童靈,很愛玩,是幼兒愛玩耍的個性,加上回到天山母娘宮認主的興奮,才會有這樣的反應。事後小琳也不知為何開文當下會一直笑,身體也動來動去,有意識的她覺得那場合並不應該笑,笑似乎不莊重,但她卻無法忍住想笑的衝動。她覺得有一個無法控制的自己,在開文時一直笑,但她自己並沒有很高興。

另一位小均(化名),是留英碩士,在貿易公司服務。她第一次的開文,一開始看起來神情頗緊繃,停頓了好幾分鐘沒有任何動作。T師姐要她跟宮壇主神祈求,讓她能順利開文,把功課交出來,否則前一段認主儀式所搏杯的金紙無法燒化,她的「冤親債主」也在等候和解的誠意。當小均在神桌前站許久不動,之後一下筆,就快速地畫出一張又一張。她也不清楚自己在寫什麼。這次的開文之後,這兩位開始到這間宮廟接受「調靈訓體」一段時間,後因理念不合而離開。
這兩位第一次所開的文,天馬行空、像自由聯想式的塗鴉。T師姐在認主者完成開文後,請她們每一張都蓋手印,她自己蓋那間宮壇的宮印,請主神認證,確認這些開文的動作,不只是自由聯想的塗鴉,而是包含與冤親債主和解的神話劇,有大批金紙將燒化,有多少冤親債主等候,等燒化完畢,「銀貨兩訖」、互不相欠,日後不能再來追討,否則由主神來主持公道。
這兩位受大學以上教育的年輕女性,由於在生活中感受到精神上有不知名的騷擾,加上工業社會謀職的工作壓力,和感情之路撲朔迷離、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來到這間宮壇尋求另一種透過超自然、通靈,來瞭解「我是誰?」。她們不只是想解決個人現實問題,也包含個人在靈性上的探索,宗教儀式不再只是尋求消災解厄。她們被資深通靈者引導,進入「冤親債主」和解的神話劇。但「冤親債主」卻成為她們在現實不順遂時,引導的資深通靈者歸因的理由。除了需要透過修行,還需要不斷花錢來消災,造成後來她們後來離開的理由之一。這兩位初入門者在T師姐引導下,將所感應到的異質性體驗(例如做預知未來的夢、在靈視中看見神佛、或不認識的過世韓國偶像明星的靈魂來找),放入自身在探索時的各種神話劇劇情,例如小琳的仙童舉止,和小均有驪山老母來教導,而做出武將般的動作。
初學者透過資深者的引導,透過一再的「開文」格式練習,讓剛入門的通靈者逐漸掌握到如何和神聖力量的「他者」(神佛、祖源、冤親債主、被吸引來的靈源等)進行溝通。通靈者自身透過所發出來的肢體動作,聲音、全身所展現的氣場以及肢體動作,在不斷練習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開文圖像從生澀到熟練的圖像布局變化,以及身體在靈性能量上,面對感應到的能量,有輕重緩急和各種情緒變化的掌握。
這些外顯出來的可見感官與肢體象徵,也讓其他同屬靈山系修行方式的通靈者,可以辨識出彼此通靈象徵的解讀,在所屬或有往來的靈性團體內,資深的可以協助資淺的,可以互相牽教、互相提攜。開文者一開始無法辨識自己在畫什麼,但隨著不斷練習,並由較資深者引導,逐漸可以學習辨識的能力。以下的個案將從女性與父權文化的家族象徵,從「開文」來探討這當中神話劇與身體展演,所意味的自我靈性的追尋。
六、開文與家族靈性救援
丁仁傑曾提出,在父系社會中的靈性權威系統內,討論到歷史演變中的神話與救贖系統敘事,包含父子、父女、母子、母女的組合[46]。在父權文化下也還有延伸到媳婦角色,以下的個例是媳婦在父系家族的角色(無子嗣無法繁衍),與她通過扮演救贖夫家祖源的角色,來找到自己在夫家父系家族象徵體系的地位。
C和H夫婦,十多年前年約40多歲,那時已經開設推拿工作室近十年,結婚多年無子嗣,尋求宗教上的原因,被通靈者告知為男方祖源作祟的問題。那段期間剛好來工作室推拿的客人通靈者比例增加,我也剛剛好在那段期間開始去他們推拿工作室調理筋骨。我去推拿沒多久之後,H開始身心不適,睡不好,好像被無形的力量所騷擾。她開始發出各種奇怪的聲音,當我邀她協助我一起記錄他們推拿客人主辦的年度會靈進香過程時,她就曾在補天宮進入靈動狀態,說了她自己並不清楚的靈語,和肢體靈動的動作,當時進香主辦者也和她用靈語對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靈動、說靈語,宛如扮演一個任性的幼兒,有別平時嚴謹自律的個性。
那段期間來推拿的幾位資深通靈者,告知她被各種外靈騷擾,她在這些資深通靈者引導下,開始感應到各種靈源,包含被告知她有一世是日本公主,還有靈源是神佛旁的仙童…等等,H和C花了不少錢去請不同宮壇處理,但並沒有解決問題。後來她接受一位常來推拿的資深通靈者Y的協助,在那位以虛空地母為主神的Y引導下,她透過開文,讓自己安頓,逐漸睡得好,不需要一直透過找他人的協助,而自己逐漸找到一條安頓她因騷擾而欠缺自信、幾乎多重人格衝突的心理。
H接受因為夫家有怨恨缺憾的祖源,騷擾了她的說法,她必須代為尋求解脫之道,以免繼續被作祟,並希望解決無子嗣問題。H開始跟Y學習開文,從最基本的開文格式、標示書寫時間和自家住址,雙掌蓋無形印、再蓋大拇指印等等。她花了一兩年透過開文和度化儀式,將夫家祖源超渡之後,還被告知必須為娘家祖源超渡。當時娘家早逝的姊姊和祖源也讓H身體不適,據Y告知,乃因這些祖源被H所散發的正能量吸引前來求助之故。但是丈夫C雖然也隨後開始通靈修行,卻只需為自家祖源超渡即可,不用為H的娘家祖源超渡。這種信仰觀對已婚男女承擔原生家庭的家族責任並不相同,顯示了現代社會女性所承受的夫家與娘家雙重角色與任務,同樣反映了通靈者受父系「家族」精神文化的影響[47]。
這張開文是H在完成為她和夫家的三代祖源開文引渡完成之後,進入新階段的第一張開文,她拍下作紀念,我去推拿時也傳給我。在這張黃紙紅字的稟文裡,在多年後對她的訪談中,她也發現,看到從自身所面臨的家族焦慮不安,到後來跳脫父權文化無子缺憾後的轉變。在那之後,她開始跟隨不同的通靈信仰團體靈修,也感應到神佛團隊來協助她的自信,讓她成為可以辨識、承接神佛指示的修行者。多年後,H透過自身對於通靈的修練與執行度靈任務,開創自己的工作機會,和朋友成立網購平台,不再只是丈夫推拿工作上的助手。
這張開文H告訴我正中央的意涵是:「虛空地母渡靈源,萬劫清源法海山。」右側: 「萬法運作平地氣」,左側:「天地運轉宇宙行」。由於當時引導H的Y師姐是修虛空地母,所以這張請虛空地母做主去運作。虛空地母這位母神,是會靈山系常出現的重要神靈,象徵滋養萬物的大地豐收、生命根源[48]。這張圖中間上頭有一炁化三清的三勾圖,和以日月代表天地乾坤,最中間是主要運作的虛空地母,左右兩邊對稱的三角和圓形符號,是神明團隊:右到左地藏王菩薩、天上王母娘娘、阿彌陀佛、藥師佛、觀音菩薩、玉皇上帝,都是靈山系常見的神聖力量。這張圖像中,各直行螺旋狀小字是透過請神佛來召喚能量,各直行螺旋狀大字部分,是引渡這些三代祖源的能量。

H寫的當下並不知道是哪些神明,事後再看這張照片,才辨識出這些神明團隊。當時指導的師姐告訴她一個初學的格式,從中間開始寫,再前面兩行,後面兩行之類的,就看個人發揮了。這張是稟文體。一般是直式,那張因為寫道空間不夠,才蓋印在下面。
那時期H所寫的筆跡有紅色和黑色,那時還曾寫過不同色的紙。例如她也被告知用白色開文紙,有醫療修復、受傷的靈魂之用。她也寫過綠色紙,是對曾殺人或枉死的祖源,她在書寫中,感受到過去的祖源、甚至自己的累世,可能曾殺人放火,透過書寫進入那種潛意識強烈的心理情結,或者進入另一種靈源集體潛意識之中。一疊開文用紙有5000張,透過大量持續書寫和燒化,讓H從開文的訓練中感受到這些祖源「他者」的痛苦深淵,彷彿H也深陷其中、感同身受的煎熬,再逐漸超拔出來。H也遇到有通靈朋友會感到痛苦,因為感應到自己前世曾是將軍,曾殺人無數,需要不斷去請神明引渡,減輕她的罪過惡業[49]。
H在新北地區出生,中學畢業後,一直也住在新北家中,和從中部北上求學畢業後謀職定居的C結婚,結婚後兩人買房在H娘家附近,並沒有返鄉和夫家父母同住,和娘家關係密切。H從無子嗣的焦慮、到夫家祖源作祟的面對,到進而為夫家祖源度化,讓她跳脫夫家父權家族的壓力,也讓H找到自己另一種自我定位,不再只是一個祖源受害者,而是可以承擔度化受苦靈魂的任務。
H所畫出的圖像,可以看出她所受到的漢人信仰文化的圖像直式對稱、渦漩的構圖影響。傳統信仰的視覺圖像,讓H一開始的開文依然遵循開文格式,但也在格式中,有個人線條變化的神話劇,感應到的神佛團隊,以及需要她協助的家族共同體的靈魂,和非家族、卻和她有緣的眾生(靈魂)。H透過「靈性資本」的運作,找到轉化她在父權社會對於男方家族的地位,扮演了宗教功能上救贖和助人的角色[50]。H在傳統的家族象徵「媳婦」的地位上,透過她通靈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救度祖源的家族貢獻,扭轉了她原先背負無子嗣的父權包袱與內心缺憾。
「祖源」是現代台灣宗教人在傳統家族共同體衰微之後,依然透過「靈」的共同體、集體文化象徵,繼續影響進入小家庭、個人主義導向的台灣社會[51]。在榮格心理學中「集體」是跨越家庭、族群、性別、世代、階級、個別文化之外的想像共同體,屬於無意識或靈性的整體感[52]。榮格所談的這些力量很抽象,像物理作用,一旦牽涉到具體的現實,例如身體的循環、筋絡、人世間的慾望變化,就變得非常具體。
集體無意識關乎個人屬於更廣大共同體的一部分,尤其是過往的靈魂的關聯。個人生命中強烈的愛恨、痛苦,會影響這個人的性格與命運,當這樣強烈的愛恨痛苦,在生命消失後如果繼續存在,就變成了榮格所謂的集體潛意識或集體無意識中,可能被召喚出來的靈性能量[53]。被召喚出來的靈性能量被個人感應到,身心受到干擾,其實漢人民間信仰認為這些強烈情感,通常是有DNA血緣關係者,被迫尋求宗教上的解決之道。
海寧格(Bert Hellinger)的「家族排列」理論裡,則看到「家庭」作為「靈魂」的共同體,有共同的動力,將曾經因為生物性的交配繁衍,所產生血緣和姻親關係,都視為家族共同體的靈魂成員。不管先後生死,都具有命運共同體的歸屬權,彼此的「靈」在生前死後繼續有所關連。這樣的共同體連結,其實也包含父系與母系祖先的連結。現實生活上原先被排除的親人,會以讓後人記起來的方式,找到歸屬的方式,讓父系與母系家族系列和諧。記憶不只是活著的人這一輩子的記憶,還包含過往的家族成員,也被視為靈魂共同體的家族同心圓的一環[54]。
透過補償逝者缺憾的因果關係與權利義務,來達到化解家族成員因逝者作祟而產生的危機感。余德慧團隊曾指出,「巫」宗教並不把受苦意義停留在漢人倫理的監控、就如精神醫療的疾病化診斷,不把意義化約到神聖力量(神、鬼、祖先、命運等等)的掌控。反而藉由重返受苦的「那個」情境,回到那個已經不在了、卻依然還繼續呼喚著返回現場的迫切感。藉由透過與「現在」因果關係共構的重返,來解開過往以來的受苦包袱[55]。
這種透過重返到個人因果輪迴的恩怨事件,往往透過儀式性的象徵轉化,來讓個體得以在想像與神話幻見中,面對負債與承擔缺憾。儀式性的象徵轉化讓個別求助者,藉由其他通靈者之助所「合演」的通靈神話事件,讓個體不斷去追尋那些難以解決的受苦源由。這種難以完成的救度任務,難以一勞永逸的不確定性,也正是人生無常的寫照。被祖源所綁架的負擔,甚至企圖擺脫累世犯錯的罪咎感,轉移了個體面對現實社會裡公共性與結構性的困境。
通靈者常強調以「家族」在世者與過世者的利益為主,強調家族秩序「孝」「悌」的實踐[56],勝過獨善其身式的個人修行,一方面壓抑構成家族繁衍最關鍵的底盤:性能量的展現,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人與其他生命體之間的能量互動關係,甚至將人之外的生命體、自然風水的宇宙能量,加以工具化,來助長以父系家族為主體的權力慾望。海邊普化儀式中通靈者對於海邊的自然生態,也只是當作協助救度眾生的媒介,尚無法將關心自然生態也納入通靈者的信仰之內[57]。
七、自我探索與引渡動物靈
在本文最後,我再提出在我所任教的大學曾舉辦的一場畢業專題中出現靈圖,來探討自我探索與引渡動物靈。這是由真理宗教系大學部學生阿辰(化名),具有幾年靈山系木公派乩身身分者所繪。阿辰透過畢業專題,執行了他入學時重要的神話劇:木公天父與瑤池金母曾諭示阿辰,在學校附近的家畜衛生試驗所,有眾多動物靈在徘徊,因此阿辰想藉由此次展演引渡這些動物靈。
這個畢業展演讓真理大學,有了一次難得宗教對話的機會。由於篇幅的限制,我把重點放在阿辰所開的靈圖意義探討,不涉及他在畢展中儀式展演部分。這個展演不同於之前這個展場的功能,阿辰將這個展場的場所精神,轉換成儀式執行的神聖空間。做為宗教系的畢業展,我對此神聖場域的轉換,所表現出來想要引渡學校附近動物靈的宗教心,感到敬佩。不過更重要的是,這個展演不只是作為一位通靈者對於他所信仰的神聖任務的執行,還包含他個人在那個階段內在自我的探究,以及這些展演對於參觀者在互動中各種意義的產出。
阿辰從他大一時,我就因為修課認識,他在修我所擔任的課程報告常出現他的靈山系宗教經驗。他大學部就學期間,我也經常看到他穿著慈惠堂的青衣服裝,髮型綁個小沖天炮,來學校上課,行色匆忙,常需要到一個多小時車程返往的宮壇協助。阿辰是個熱心、講話直接、敏感、有正義感又行事衝動的年輕人。直到那次的畢展我才有機會,現場看到他儀式展演,和他說明現場佈置的靈圖,了解一段年輕世代通靈者的自我追尋。我只舉其中兩張靈圖來探討。因為這兩張靈圖牽涉到通靈者自身對存在處境的書寫造型,以及反映了作為一位乩身所承接使命的符號構圖的意象探索。
阿辰是台灣紫天道脈木公派的乩身[58],據他自述,年幼時不會說話,家人曾前往宮壇,由開天九龍三童子附身堂主告知勿念[59],幾天後開始說話。退伍後,在準備大學入學考試的過程中,每天晚上都會夢到五個字「無極紫天宮」,當他到了「那沒有盡頭的階梯,心裡萌生退卻的念頭,但心想又想把這個答案找出來。當下決心 要一定上去『無極紫天宮』,一階一階的慢慢走上去,終於到了無極紫天宮,我到了我在大殿,慢慢失去意識。」[60]
阿辰後來醒來得知,被開天九龍三童子訓體,之後一段時間剛開始由開天九龍三童子訓體,漸漸開始通靈,之後靜坐時就「換木公天父來教點地脈、啟靈、點主等功夫」。他曾到同樣是木工派門的無極明聖宮請事翁素雲師姑一年後,再受到無極紫天宮木公指示,回去聖德慈惠堂承接堂務、打理雜務。但因故離開,回到無極紫天宮精進自己,透過精進自己來提升能力助人[61]。
這兩張黃紙上以血紅色筆跡描繪的靈圖,根據阿辰的說明,第一張是說明「日月天地共同映照,四方萬物歸同源」,「萬靈萬物從中心點出發到外圍,但也會從外圍回歸到中心點」。第二張的圖和第一張相接,是第一張中間的像漩渦狀環形圖的特寫。第二張圖和第一張的宏觀大宇宙的視點布局不同,第二張帶有描繪從展演者「我」的生命史為中心的小宇宙,去關聯到大宇宙的神話象徵。阿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歷程,一方面被捲在這滾滾紅塵之中,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可以協助神明「救靈收圓」[62]。

這兩張圖在繪製過程,阿辰的內心並不平靜,有很多牽絆和情緒,讓他的靈圖充滿急促潦草的筆觸,希望趕快畫完的催逼。這兩張靈圖據他個人自述,也反映出他個人在那段時期曾經感情受挫,陷入情慾漩渦中,必須花時間走出漩渦。他自述:「如果我過世時我還是會再走過這個漩渦,測試我自己有沒有放下這個阻礙。」這裡觸及到通靈者個人所參與的生命史流變,與所扮演的神話劇角色在靈源中的神話地位,具有回顧自身死後靈魂的價值重估。再者,阿辰也希望「透過這些靈圖,來教化這些靈體,試著放下罣礙及怨氣,讓自己離苦得樂,各歸本位。」[63]在此,阿辰表現出作為神聖代言者所承擔的角色,去執行救渡受苦靈體任務的自我期許。
如果讓我們回到前面杉浦康平提到的,在「靈」的作用下,「形」變成有血有肉的「型」,產生蓬勃生機的搏動。這種能動力的激情展現在阿辰的靈圖筆觸之中,帶有急促、未完成的不確定感,希望濟世度靈,卻又展現出自身的有限性與不安。第一張圖上半部的日月、中央的神聖力量運作,中間與下方的渦漩、曲線、方線,在對稱的力量中,線條聚合收縮,充滿不確定的慾望騷動的奧秘。一種想要關照安頓秩序、卻又力有未逮的搏鬥。這張也像一張悠遊上下四方、卻又迷途、徘徊、處處為家的遊戲塗鴉之作。
這樣的圖像張力並非像那些公開展示的宗教圖象,所給人的穩定與秩序感,相反地,這種靈圖又像遊戲、又像未完成、又像塗鴉,反而呈現出一種意義的不確定。這樣的靈圖反映出開文者內在拉扯的慾望張力。一般傳統宗教畫,要符合正規的製式化構圖,把個人很多情緒控制、壓抑或是轉化。阿辰的靈圖透露了潛意識的探索、尋找解放自身與他所想要解放的受苦動物靈,以及難以理解的慾望奧秘的線索。
阿辰在籌備展覽時,只有一位和他同組的同學協助,其餘同學不知何故,並沒有來協助。可能是牽涉到班上同學所難以介入的宗教領域,也可能是阿辰平時的行事作風,常常一個人攬著做,不知如何請他人協助。在整個佈展和展覽過程,我可以感覺到他有既排斥、嫌麻煩,又不得不做的矛盾。加上展場空間並不小,所以他花費不少心力、體力,自己獨當一面。我猜想他還要承擔學校功課,和宮廟的廟務,還有協助信徒辦事,一副沉重的無奈感。
那時,我也不大清楚這位不情願的同學,為何又要做這件吃力不討好的儀式展演,後來看到他的報告書,了解到來自他的主神木公要求的使命,讓我感到敬佩與慚愧。這是一間基督教長老教會設立的大學,但是這些年來校方似乎很少對於鄰近校園的家畜衛生試驗所,有進行生命教育課程上的提醒。我曾多次聽到遠處彷彿是動物的慘叫聲,心裡感到難過。沒想到這位被迫度動物靈的同學,盡他能力所及,在本校的牛津學堂後面的展覽空間,完成了引渡動物靈的儀式,還是透過有畢業學分的畢業專題。
在阿辰的報告書中,他坦承剛開始接到要擺盤度動物靈時,其實很不想,因為他知道儀式展演的準備,只有他一人相當費事。但「木公天父」讓他頭很痛,他只好承接這個使命,過程相當辛苦[64]。那時做為指導老師的我也求好心切,覺得他所畫的靈圖,有點簡略草率。但過了這些年,再重看他畫的靈圖檔案時,我猜測,那可能正好反映了當時他矛盾的不得不做,又難以靜下心來的真誠寫照。
另外,我還感受到阿辰有另兩層的負擔,一層是對這位乩身同學來說,度靈必須承擔那些引渡靈魂的痛苦,那些被虐而死、被拋棄的動物靈,是如何痛苦地向他哭訴。這些強烈的負能量、負面情緒造成他的負擔。另一層是他當時還在自己的感情創傷之中,尚未平復,這些生命的內在情感的糾葛,可能藏身在這兩張靈圖之中。
我選擇阿辰來做為本篇文章的最後一個探討主題,因為這牽涉到同樣是基督教大學,如何從對神聖、對靈魂、對苦難、生死的感知與關懷,去看待我們作為一位陪伴年輕學子一起追尋生命意義的「教學者/夥伴」身分。開文與神話劇的通靈現象,反映現今社會中,人與自我和他者溝通,一種既追求解脫、又產生控制的矛盾張力,也意識到通靈對於無神論現代教育的提醒。
這些開文圖像以及背後的神話劇的儀式展演,反映了個體生活在現代社會中,如何一方面去面對個人現實處境的考驗;另一方面,個人被迫超越了自我的存在處境,能和被工業社會遺忘的天地自然、神佛、過世靈魂相溝通,度化受苦之靈,展示出自古以來這些難以被看見、定根於現實、稍縱即逝的庶民生命美學。
八、結語—平凡中不平凡的自我期許
近代以來的西方哲學,人自覺到自身的主體自主性,是任何權威—即使是神的權威–都無法壓抑的。學問、藝術、政治、倫理等所有領域的原理,從宗教的地盤獨立出去,開展出人類生活的「世俗化」[65]。我們現在的學校教育也是如此。上述這些透過通靈者開文與相關的神話劇,都牽涉到「我是誰?」和「我們是誰?」的自我追尋。「圓滿不是超越而是接納」[66],這不只是獨立自主的人的自我認識,也是一位平凡者透過自身所感應到的神聖他者,激發自己去關懷過世的受苦靈魂,不管自願還是被迫。這當中有神聖的權威對於人做為能動主體的限制,但也透過神聖權威讓人做出原先不會做出的行動,去接納受苦的他者,甚至為祂們尋求解脫之途。
如果宗教作為一種幻覺,那這種幻覺的確是讓我們這些平凡者,有了重新看待自我、死亡、死後生命的機會,讓死亡不是虛無,而是人與「自我」與「他者」進行溝通的另一扇門。儘管對於現實工業社會,面對每天無常地生命不斷殞落,平凡人束手無策。透過通靈,來達到對於不幸與受苦尋求解脫的幻想與盼望,是一種逃避,也是一種慰藉,生命與生命之間並不孤單。這篇文章還沒有去探討通靈者因為通靈所產生的各種自我傲慢的面向,這是權力意志鬥爭的另一種現象,也是自我幻覺不平凡的危機所在,值得未來繼續探究。
[1] Michael Richardson, Georges Bataille (London: Routledge,1994), p.107。
[2] 西谷啟治,《宗教是什麼》,陳一標、吳翠華譯(台北:聯經,2011),頁21-22。
[3]同上註。
[4] 羅布.普瑞斯(Rob Preece),《榮格與密宗的29個覺–佛法和心理學在個體化歷程中的交叉點》廖世德譯(台北:人本自然文化,2008),頁132-136。
[5]《榮格與密宗的29個覺–佛法和心理學在個體化歷程中的交叉點》,頁136-139。
[6] 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台北:聯經,2009),頁108-112。
[7] 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台北:前衛,2016)。
[8]本節改寫自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頁23-29。
[9]默西亞‧埃里亞德(Mircea Eliade),《世界宗教理念史(卷一):從石器時代到埃勒烏西斯神祕宗教》(Histoire des croyances et des idées religieuses I : De l’âge de la pierre aux mystères d’Eleusis),吳靜宜、陳錦書譯(台北:商周,2001),頁389-390。
[10]《新約聖經‧使徒行傳》(二 4 ,四 8 、 31 ,六 3 ,七 55 ,九 17 ,十一 24 ,十三 9 、 52 )、艾倫伯格(Henri Ellenberger),《發現無意識(Ⅰ)動力精神學的源流》(The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Psychiatry),劉絮愷、吳佳璇、鄧惠文、廖定烈譯(台北:遠流,2003),第一章。
[11] 《山海經‧大荒西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
[12]I.M.Lewis, Ecstatic Religion: A Study of Shamanism and Spirit Possess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13]石素英主編,《基督宗教與靈恩運動論文集》,台北:永望,2012。石素英主編,《穿越傳統的激烈神聖會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靈恩運動訪談紀錄》,台北:永望,2012。
[14]林美容、李峰銘,〈臺灣通靈現象的發展脈絡:當代台灣本土靈性運動試探〉,《思與言》53卷第3期( 2015.09),頁5-46。
[15] W. T. Stace,Mysticism and Philosophy, London: Macmilian, 1960.中譯本:《冥契主義與哲學》,楊儒賓 譯(臺北:正中書局,1998),頁9。
[16]Mircea Eliade,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Trans. by R. Sheed (New York: Sheed & Ward, 1958), xii.
[17]Lewis, I. M. Ecstatic Religion: A Study of Shamanism and Spirit Possess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三版前言。參見陳家倫,〈臺灣新時代團體的網絡連結〉,《臺灣社會學刊》36(2006.06),頁109-165;林美容、李峰銘,〈臺灣通靈現象的發展脈絡:當代台灣本土靈性運動試探〉,《思與言》53卷第3期( 2015.09),頁5-46。
[18]呂玫媛,〈當代媽祖信仰的個人化與宗教性:以白沙屯為例〉,收錄於《日常生活中的當代宗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台北:群學,2015),頁79-147。
[19]林美容、李峰銘,〈臺灣通靈現象的發展脈絡:當代台灣本土靈性運動試探〉,頁23。
[20]諾伊曼(Erich Neumann)《大母神-原型分析》,李以洪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4-5
[21]Mircea Eliade,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Trans. by R. Sheed (New York: Sheed & Ward, 1958), xii.
[22] 詳見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第四章 能量的戰場──海邊「普化」儀式探討。
[23]高夫曼(E.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徐江敏等譯(台北:桂冠圖書,2011),頁12-13。
[24] 島薗進,《由救贖到靈性︰當代日本的大眾宗教運動》,丁仁傑, 姚玉霜, 陳淑娟合譯(台北:聯經,2020),頁360。林瑋嬪,〈都市神壇與乩童靈力:桃園八德的例子〉,收錄於《日常生活中的當代宗教:宗教的個人化與關係性存有》(台北:群學,2015),頁187-233。
[25]詳見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第四章 能量的戰場──海邊「普化」儀式探討和第五章 神話口述與通靈象徵──「天山老母」女乩現象。
[26]王鏡玲,〈「肉身空間」的顯現–淡水龍山寺普渡祭儀初探〉,《輔仁宗教研究》,第26期(2013.03),頁31。
[27]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頁199-200。
[28] 在此是指通靈者自身因感應的個人神話角色,而展現對應的肢體語言象徵。
[29]王鏡玲、蔡怡佳合撰,〈神聖與身體的交遇:從靈動的身體感反思宗教學「神聖」理論〉收錄在《身體感的轉向》,余舜德主編(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176-177。
[30]王鏡玲、蔡怡佳合撰,《身體感的轉向》,頁177。
[31]通靈者的個人或團體一旦出現在傳統廟宇的慶典或是廟內,他們的靈動與身體的神話劇展演,除非是來到認同的信仰團體的場所,否則往往被視為秩序的擾亂者,而被禁止。
[32]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頁233。
[33]王鏡玲,《慶典美學》(台北:博客思,2011),〈慶典美學與中元普渡〉。
[34]卡爾‧榮格(C.G. Jung),《心理結構與心理動力學》,關群德譯(北京:國際文化,2011),頁142。
[35]杉浦康平,《造型的誕生》李建華,楊晶譯(台北:雄獅美術,2000),著者序。
[36]杉浦康平,《造型的誕生》,前言。
[37]杉浦康平,《造型的誕生》,頁170
[38]改寫自德勒茲(G.Deleuze)加塔利(F.Guattari),《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輝譯(上海書店,2010),頁154。
[39]詳見《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第四章 能量的戰場──海邊「普化」儀式探討。
[40]參見https://pa00002.pixnet.net/blog/post/18606400。 我之前訪談一些通靈者的看法也與此類似,參見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第四章 能量的戰場──海邊「普化」儀式探討。王鏡玲,〈神聖的顯現–母神、家族象徵、靈界〉,《哲學與文化》41卷10期(2014.10) 頁33-57。
[41]改寫自王鏡玲,〈救度靈界–海邊普化儀式的現象描述〉,《輔仁宗教研究》30( 2015.03)頁25-62。
[42]同上註。
[43]王鏡玲,〈神話口述與通靈象徵–「天山老母」女乩現象研究〉,《臺灣宗教研究》14:2(2015.12),頁65-93。
[44] 同上註。
[45]同上註。
[46]丁仁傑,《民眾宗教中的權威鑲嵌: 場域變遷下的象徵資本與靈性資本》(台北:聯經,2020),頁516-522。
[47]王鏡玲,〈神聖的顯現–母神、家族象徵、靈界〉,《哲學與文化》41卷10期(2014.10) 頁33-57。
[48] 關於地母系的探討,李峰銘,《走靈山的女人:臺灣新時代薩滿「靈乩」的民族誌分析》,臺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5),頁81。https://www.wujicimutang.com/289612699734395313542232027597.html
[49] 根據2021年11月對H的訪談。
[50] 丁仁傑,《民眾宗教中的權威鑲嵌: 場域變遷下的象徵資本與靈性資本》,頁516-517。
[51]參見許烺光著,《祖蔭下》(Under Ancestor’s Shadow),王芃、徐隆德合譯(台北,南天,2001),頁208。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頁31。
[52]卡爾.榮格(C.G.Jung)主編,《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龔卓軍譯(台北:立緒,1999)。
[53]卡爾‧榮格,《心理結構與心理動力學》,236-244。
[54]伯特.海寧格(Bert Hellinger)《心靈活泉:海寧格系統排列原理與發展》霍寶蓮譯(海寧格機構,2009)。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頁31。我個人也曾參與過海寧格家族排列工作坊,感受到家族成員之間愛恨慾念,對於個人生命史的影響。
[55]詳見余德慧,《台灣巫宗教的心靈療遇》(台北:心靈工坊,2006);蔡怡佳,〈在非現實母體中悠晃–余德慧的宗教療癒〉,收錄在《余德慧教授紀念學術研討會文集》(台灣大學心理學系2012.12)頁85-101。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頁32。
[56]羅臥雲,《瑤命皈盤》。台東:慈惠堂寶華山翻印,2008。
[57]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頁32-33。
[58]木公亦作東王父、東華帝君、東父、東君、木公、扶桑大帝、青童君、青提帝君等,是中國神話上的仙人,傳統上與西王母相對應。關於紫天道脈,見李峰銘,《走靈山的女人:臺灣新時代薩滿「靈乩」的民族誌分析》,第三章 「會靈山」的變貌:靈脈的角度。
[59]根據阿辰的畢業專題展演報告書。有關九龍三童子的形象之描述,各家宮廟會降不同的說法。根據李峰銘引無極聖功的說法是:「九龍三童子」是由「一炁玄童」後來再演化而出。「一炁玄童」其實就是「東王木公」去老返童所演化出來的童子。而九龍三童子分別是掌印童子、掌日童子、掌月童子。大童子也就是掌印童子,巡按辦事為蓮花轉世;二童子為掌日童子,葫蘆收靈、麒麟護世;三童子則是掌月童子,金槌驅妖,九龍顯世。李峰銘,《走靈山的女人:臺灣新時代薩滿「靈乩」的民族誌分析》,頁70。
[60]畢業專題展演報告書。
[61]同上註。
[62]同上註。
[63]同上註。
[64]同上註。
[65]西谷啟治,《宗教是什麼》,頁52。
[66]羅布.普瑞斯,《榮格與密宗的29個覺–佛法和心理學在個體化歷程中的交叉點》,頁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