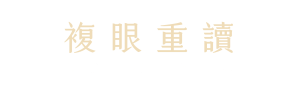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吳明鴻(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候選人)
當代人類學討論受苦與療癒的議題有著極大的挑戰。
當人類學家繼續從他所擅長的文化表徵、族群衝突、社會結構、性別宰制、政治經濟或宗教實踐等社會文化條件來解析個體或群體的受苦叢結(complex)時,苦難的主體卻總是肉身的、個體的、具體的、殊異的、處境性的、倫理的與地方的。八〇年代起,人類學家有意識的在這兩者之間抽絲剝繭,進行解釋性工作並尋找苦難的社會根源,甚至透過多點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的田野工作和書寫形式,把全球趨勢、國家層級治理、區域特殊歷史的和個別家庭境遇做了多層次的併置(juxtaposition),指出其間相互影響的方式,呈現出一幅幅極度複雜又無比堅實的受苦網絡。
苦難的解釋:如何不旁觀他人痛苦?
問題出在「解釋」一事。例如,當我們提出類似「新自由主義市場化力量下,人也被從生產力與產值的觀點來評估和管理,使得人口被數字化與量化,間接導致了大量的社會遺棄(social abandonment)現象」[1]這樣的主張時,我們是在用巨型的、結構性的力量來解釋掉(explain away)經驗現象,卻無法從該解釋中得知:這一切是如何在具體的社會運作中被「做成」的(be created/be made)?又是如何被一群地方脈絡下的行動者所經驗、活出和社會地互動出來?換言之,這種對現象的解釋,無助於掌握真實世界中特定社會關係和主體經驗如何開展的知識建構工作——它太「高」了。
這將會相當可惜。一方面,當人類學揭諸苦難的社會因素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時(這在苦難被心理化和個體化的年代的確是個創見),它顯得過於決定論(deterministic),只是讓現實顯得更加無望,人們被盤根錯節的外在因素給綑綁,幾無逃脫的可能;另一方面,這樣的學術生產也讓人失望,因為它提出問題,卻無能給出解方,或其解法在現實中實現的難度太高。與此相似,當醫療人類學(medical anthropology)繼續停留在「疾病的社會建構」的分析視角,傾向於肯認「症狀作為抵抗」的主張,而忽略或反對精神醫療體制過度病理化存在領域的霸權時,它將無法處理精神病生理症狀對主體自身及其周遭環境所帶來的真實毀壞力道,且隱約與諸多醫護人員在專業上和人道上的努力相對立。最後,它只能提供批判性解釋,卻喪失介入現實的力道,因而無法貢獻於其所允諾的照護與療癒。
內捲:民族誌認識論
印度人類學家Veena Das覺察到這個問題,她的苦難人類學可以說是一種觀察複數力量(forces)如何內捲(involution)的民族誌方法。若用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語彙來說明——「中介即轉換」(mediation as translation)(Latour 2012[1991]:191-206):任何巨型力量要進入相對在地社區、家庭和人際實作中,就必然有一個經由在地貧困處境、親屬關係、地方政治、宗教文化捲入和中介的過程,一定會產生地方層次的生產和變異,使其被該社群所挪用/佔有(appropriation);而若到了個別家庭和個體的層次,又更是另一層次的中介/轉譯。因此在概念上,這將不會是一個單純的映射(reflection)的關係,例如,把「家庭」視為一個「微型國家」(mini-state),彷彿家庭作為國家權力的倒影或代理人(agent),被用以執行對「無用人口」的「檢傷分類」和「拋棄」的行動。
並非這樣的宣稱是錯誤的,真正的問題在於,它顯然錯失了「事情是如何在具體處境中開展(unfolding)」的問題,這樣的世界又如何被身為血肉之軀的行動者協同打造出來?其中,幾個關鍵的問題包括:這些社會遺棄事實如何在這些「拋棄者」家庭成員間的倫理關係中成為可能?它是否以某些醫療、藥物、疾病知識甚至是民間常識(common sense)作為條件?又如何在親情聯繫與家內政治之間折衝與協商?也只有這樣從地方的、關係的、實作和互動的領域追問進去,我們才能理解新自由主義何以對貧窮群體的衝擊遠大於中產以上階級。
疾病的本體:關係網絡中的特異地帶
Das的Affliction: Health, Disease, Poverty一書有兩個關鍵概念,它們就是這本民族誌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疾病的傳記(biography of illness)(Das, 2015: 208)和治療的地理(therapeutic geography)(ibid.: 222)。作者超出了從病人主觀的角度去討論生病敘事(narrative of illness),這是過往醫療人類學主要路徑之一,她不預設主體=人或文化,而是將「生病事件」作為一次組裝(assemblage),去談包括個體生命在內的多重力量的匯聚、錯接、交集而形成的地帶(region)。如果有所謂「瘋狂主體」的話,那麼該主體並非在個體身體裡,而是座落於這個張力地帶。兩個概念中,「傳記」是時間中的軌跡,而「地理學」則是空間中的路徑,疾病病程既開啟了一連串時間中的轉折、狂飆或停滯的動力關係和歷史,也啟動了「尋醫」旅途的無數空間路徑的迂迴和交疊。在此,疾病作為事件,將人、事、物席捲而入,進入到一個生成(becoming)的地帶,而瘋狂作為生命之於社會世界的溢出,其話語有雙重涵義,不只是該地帶難以棲居(dwelling)的表達,更是回到存在的規範性領域的努力。
這是一種回到本體論(ontological)層次的對疾病的人類學探究,不過這並非靜態的本體論,而是實作的和生成的本體論。基礎提問是:就在地人的生存而言,疾病(disease)意味著什麼?生病(illness)由哪些事物構成?對人類學家來說,這些問題唯有透過田野工作才能回答,而且還會一下子就會拉出了包括文化表徵、肉身實作、社會互動、醫療專業、國家治理等相互交纏的網狀結構來。在Das這裡,疾病的組成或瘋狂的主體首先是一個諸多關係網絡之間的特異性(singularity)的地帶,是諸多可能性條件的匯聚下的偶然生成,而「主體性」作為一個場域、一個不同勢力爭奪、橫越其上的戰場(Das 2015: 84)。在此,主體性不是既定的(given),也不是只是一般所認定的人類的主動/能動特性。
具體說來,疾病與病程必須通過貧窮鄰里的醫療和公衛條件、家庭生計困窘、性別壓迫體制、在地巫術文化和親屬關係等條件形構自身。Das在本書第三章討論精神疾病的案例中(Das 2015: 82-112),一位母親不再成為「母親」了(因為她希望自己所生出的兒子可以死去),她的兒子不再被當成「兒子」(他對母親和妹妹動粗,且被懷疑遭巫術詛咒而擁有野獸般的蠻力、毋須進食的身體和異常長的手臂和狂暴的性格),甚至不再具有「人」的位格。許多的「是什麼」(或「原本是什麼」)變得不太穩定,甚至在某個精神狂躁的暴力事件處理中,母親也痛心疾首的哭訴,當下,自己的先生變成了「兒子的父親」而不再是「我的丈夫」。本體論層次的關照使我們發現,當疾病進到貧窮鄰里和底層社會反而造成「本體的動搖」。
本體的動搖:「規範上正常」的影響力
另一個與此相關的民族誌片段是關於「正常」(normal)的討論:Das指出了規範上的正常(normative normal)和病理上的正常(pathological normal)間的關係性(Das 2015: 82-112):民族誌主人翁之一的Swapan是一個考試失敗、已經二十歲卻不願意出去工作的年輕人,他無法成為帶來家庭經濟產值的一員,總惦記著自己過往「好學生」的光環,繼續夢想唯有讀書升學才是希望所在,但埋頭苦讀、精神壓力和考試失敗的事實,附加以母親的不滿和鎮日冷嘲熱諷,使得他的家庭關係和社會處境越來越孤立,衍生出日益嚴重的、對母親和妹妹的暴力行為——他在「常規上正常」的標準上失敗了,因而進入了病理的領域,而最後卻弔詭的因為在「病理正常」的量尺上痊癒/出院了,「掙回」了回歸社會和家庭的(常規正常)的地位,即使,後來的他依然每天抱著英文字典研讀,繼續寄託於那個不可能的未來。
Das用現代性魅惑(phantasmal modernity)概念指出,類似現象在印度底層社群層出不窮,「教育帶來階級翻身」是一個極大的誘惑:對貧民區子弟來說,這並非遙不可及,「只要努力一定可以……」的意識十分普遍,但現實中,多數家長和學子期待的教育翻轉之路都是失敗的,但這個夢想卻不成比例的膨脹,成其強勢、無可取代的精神象徵。
在此,「應該是什麼」的規範性力量動搖了原先「是什麼」的存在秩序和社會關係的確定性——瘋狂的力量特別寓居於此。另一個少女的案例則與Swapan案例相反:一位原先溫馴懂事、名列前茅的小女孩,到了青春期之後卻被評價為違逆長輩和行為偏差,家人認為很可能遭到惡靈附身,因此長期遭到父親的毒打和精神虐待,連鄰居都看不下去而出面勸告。然而,其「不正常」的評價有其背景:在危險的性騷擾和性暴力的社會環境下,父親只要一沒看到女兒人影,就懷疑她去會見小男朋友,極盡監控、奚落和精神虐待之能事;而極度寵愛男性孫子的奶奶則對她的成績光彩和平時花大把時間唸書一事嗤之以鼻,並認為那會「讓女生腦袋燒壞掉」,是「極度危險的事」。在三四年間的身心虐待後,少女考上了大學先修班,她成績表現實在太優秀了,以致父親最終放行、讓她去升學,得以離開家中,Das也在經濟上支持她完成大學學業,後來成為一名專業護士。與前例相反的是,這個女生是用世俗的成就來證明、甚至「平反」自己的「正常性」,也以此避開了精神醫學的病理與醫療介入領域。
希望:那尚未被決定的、那充滿孔洞的……
如果受苦的民族誌能夠帶給我們一絲希望,那麼它應該寄託於民族誌故事中無比重要的雙面性:一方面,在「疾病傳記」或「治療地理」中顯示出所有超乎個體的力量是如此盤根錯節、交互纏繞,而人的悲慘命運似乎又充滿了偶然的必然性;另一方面,當我們看到Das如何涉身其中、審時度勢,時而驚呼於個人命運的轉折(例如某個危機時刻,Swapan的大伯竟然說服了他去住院一事)和不可預期性,我們理解到,所謂的「特異地帶」指的僅是可能性條件(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的匯集,但它並不是決定結局的充要條件。正是在此,殊異的生存技藝、機遇和偶然性、時空環境,甚至處理不預期的特定問題的現實需要等,都會參與進來,一同決定那尚未被決定的。
唯有到了這樣的理解時刻,「照顧」在人類學的貢獻中才得以成立,也唯有走到這一步,民族誌知識才超越「旁觀他人苦痛」,得以挖掘出生命另類可能性的機巧,而真正走到一個能夠與(致力於照護的)助人專業或實務工作並肩作戰的知識位置。
參考文獻
Das, Veena. (2015). Affliction: Health, Disease, Povert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譯)(2012)。《我們從未現代過》。台北:群學。(Bruno Latour, 1991)
葉佳怡(譯)(2019)。《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新北市:左岸文化。(João Biehl, 2002)
[1] 這個例子出自Veena Das(2015: 18),他對João Biehl(2019[2002])的《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Vita: Life in a Zone of Social Abandonment)一書中對「社會遺棄」現象的解釋方式感到不滿,透過對前者的批判來提出自己的方法論主張。這篇文章的靈感即來自於這個方法論的區別,後續行文將繼續透過該案例的討論凸顯出本文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