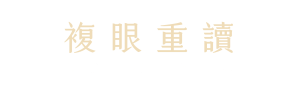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司安妮(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生,目前在進行博士論文的訪談和書寫的階段,主題與創傷、生命史相關,同時也在上海大學的心理輔導中心實習,接受精神分析取向的訓練和督導。)

「聽」與「說」是心理治療當中的基本行動,在筆者進入心理學系學習後,這兩件事就是老師一直在叮囑的,是基本功的存在。關於怎麼聽,聽什麼,聽到什麼?「聽」到底是一個行為,動作,一個技術嗎,還是什麼?從佛洛伊德開始就給了我們很多的靈感,分析師的傾聽是要「平均懸浮的注意力(evenly suspended attention)」,分析師要對病人所說的浮現出來的內容保持同等的注意力。拉岡的L圖示也標示出分析師與分析者在分析現場的互動,分析師的聆聽往往會處在小他者的位置和大他者位置的移動之間。
除了在諮商情境中的「聽」,聆聽也發生在做研究的過程中。那天在和同學討論我們所收集來的訪談材料,同學在謄錄錄音之後,將語句不通順的地方以可以被閱讀的方式作了修改。當下我說這不就是像做量化研究竄改數據一樣的行為嗎?對做質性研究來說,我們到底如何處理以及看待我們所收集/經驗的這一些訪談素材/文本,受訪者的話語是data嗎,是一種怎麼樣的data,聽的經驗如何被寫?
這是我在心理諮商實務和研究田野過程中關於「聽」的情境,鷲田清一的這本《聆聽的力量》從臨床哲學的角度試圖與哲學本身對話,對「聆聽」作了一系列的自由聯想,希望藉由閱讀這本書來打開對於聆聽這件事的認識,對於前面的情境有新的視野。

走向他者
鷲田清一站在哲學的出發點上,從象牙塔、學院裡,走向了人群中,走向了現場,提出了「臨床哲學」的概念。「臨床哲學雖然也站在人們『受苦的場所』,但並不試圖成為治療的學問。對臨床哲學來說,眼前正在『受苦』的這個人,是否為需要『治療』的『患者』?甚至連這件事也不是不證自明的。臨床哲學要做的是與受苦的人對話,和他一起思考。(69頁)」他又說到「臨床哲學不是以治療為目的⋯⋯而是和受苦的人一起扛起問題,和他一起分析、理解、思考。透過這樣的作業,從問題的內側克服問題,找到克服問題的力量。(70頁)」透過「聆聽」帶出臨床哲學的可能性,這一點對哲學的發展來說突破了哲學長期以來對說理(Logos)和對話語內容的執著,而強調了「話語的肌理」(36頁)。比起哲學原本給人帶來的距離感,鷲田清一好像離受苦、受苦的人,又更近了一點。而臨床哲學又拋開了心理治療或精神醫學的「包袱」,不需要以治療作為目的,不需要以治療成效等來彰顯自己的有用,這樣的思考,是否能給心理治療帶來某些解放或鬆綁呢?
鷲田清一重新打開對哲學的場所的想像,「哲學不應該是退入到自己的內部,播放並觀看自己的意識或思考——這種行為,經常被稱為『反省』(reflection)——正好相反,我們不能允許自己敗退、撤退到這樣的內部。主體必須和他者一起,處在相同的時間和空間;即使那只是一時的關係也不離不棄,持續在現場思考。所謂哲學的『場所』,不正應該是這樣的地方嗎?(72頁)」這也讓我想到對於人的想像,從原子化的方式來到了以某種關係的層面來思考,那並非在自我的內部的孤獨的運轉,而在主體與他者共在的場。如果以聆聽來實踐臨床哲學,那麼就是「我」與另一個他者,處在相同的時間和空間,持續在現場思考。「與他者的時間挫合為一體,和他者一起經歷共同的時間,在這樣的共時關係中,以哲學思考和他者『一起經歷苦難』(sym-pathy)(72頁)。」複數的主體在現場共同經歷苦難。
聆聽是與他者遭逢的界面,在聆聽中,開啟了「我」與他者共在的空間。在心理諮商實務中,常常會出現一種矛盾,要把案主拉到諮商師的世界中,還是諮商師要進入到案主的世界中?在醫院這樣的場域中,容易出現將病人/案主作為某種治療的對象或客體的觀點,醫生根據症狀開藥,但卻沒有太多的時間了解病人的脈絡,或是病人以藥作為一種快速解決症狀的方式而忽略了其他方式來了解自己。在一年的心理評估的工作裡,我常常被案主當作是一個有著專業外衣、可以判定案主是否有病的對象,我也不停得問自己,究竟如何看待精神疾病,以及人們對此的想像。我作為一個專業工作者,究竟我更相信我所學的理論、知識多一點,還是我更相信眼前的人多一點?甚至來訪往往會撞擊我們所學的東西,例如在學校裡,要實施自殺的案主對前來協助他的諮商師說,「我活著還是死了對你來說只是你的工作」⋯⋯我曾聽朋友說自己與學輔中心的心理師晤談之後,因為10多年前的家暴,於是心理師要通報,朋友不解家暴已經是10多年前的事情,不知道現在通報有什麼意義,而且自己也已經有兩位社工師在陪伴,然而心理師則覺得他可以獲得資源,可是當時朋友希望申請的是特教學生的資格⋯⋯在專業的想像和實際互動的人之間,「我」的位置在哪裡?「我」要如何回應?如何反思因結構的壓力或約束帶來的意圖的變形?如何想像一種他者的心理學?

語言是思考與情感的身體
閱讀鷲田清一的書時,常常讓我覺得不只是在讀一本關於臨床哲學的論述,而會覺得透過文字給我帶來一種思考的體驗。
讀到第六章時讓我覺得很欣喜,這一章在談「觸」和「碰」,這兩種都是身體的感覺,然而鷲田清一用「觸」和「碰」來談聲音、話語帶來的身體感。
作者首先談到了一件怪事,是一名少女無法入睡,多年來看診的醫生也束手無策,少女的醫師拜託他的朋友,另一名精神科醫師,一同前往問診。兩位醫師抵達少女的家之後,醫師先為少女把脈,一分鐘120下,這位醫師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少女入睡的時候,一手把著她的脈搏,一手抵著腳底,漸漸得醫師的脈搏也與少女同步了,一分鐘120下。這也喚起了醫師的困惑,因為假如一般人在這樣的脈搏下,是會呼吸困難的,然而醫師卻覺得時間流動緩慢、意識也更清晰,而就在這個時候,醫師聽到外面母親為了招待醫師而在廚房炒菜的轟隆聲,「不斷傳來的轟隆聲,簡直就是痛苦本身(168頁)」⋯⋯
借用這個例子,鷲田清一討論了其中的「同步性」,少女對於環境是毫無阻隔的輸入,彷彿環境的嘈雜同步到身體的節奏中,另外,中井久夫這位醫師與少女的身體節奏在觸碰中也具有了同步的節奏。
接著鷲田清一搬出了日文裡面的用法,中文裡的「交流」,在日文中是「ふれあい」,這是由「ふれ」(接觸)和「あい」(相互)組成的,「乍聽之下是一個很美的字詞,但它裡面卻包含著極其恐怖的『ぶれ』——動搖(169頁)」 。
鷲田清一試圖在談的是,話語不只是傳遞訊息、或是在符號層面的互動,「同時也是能觸碰我們的聲音」,而這個觸碰也不是僅僅只是「送達」,「不只是聲音在發聲者和接收聲音者之間的移動」,不僅僅只是這樣的移動,「發生在雙方身上的同步、共鳴與共振,讓人的存在發生巨大的動搖,終於讓兩個身體有了瞬時的『接觸』(170頁)」,這個共振是會使人的存在發生動搖的。而這裡的「終於讓兩個身體有了瞬時的『接觸』」,不免讓我想到在第二章裡說的共時性、複數主體相互接觸的場所,「與他者的時間挫合為一體,和他者一起經歷共同的時間,在這樣的共時關係中,以哲學思考和他者『一起經歷苦難』(sym-pathy)(72頁)」。但是這裡的意象——「兩個身體」,而不是前面篇章常以「複數主體」來概括談論的對象,我認為有某些其他的意涵和面向是作者想要拓展的。
「觸」和「碰」一下子展開了聯想的空間。
在重讀了幾遍「觸」的這一小節時,我會覺得有很多東西從四面八方過來,也激起了自己不同區域的活躍,比如有些時候感覺話語落在肩上,有些時候大腦會很活躍,有些時候會有心的觸動,有些時候手會拿起筆要劃下某些話語,有些時候看著看著視線會從書上移開想要望向遠方⋯⋯或者也可以說,好像有很多東西往四面八方去,記憶往內、視線往外、沈重往下⋯⋯並非是從視覺到大腦的純粹連線,那也是鷲田清一對我說話的一種狀態。從護理師實施的包裹療法,坂部惠的「觸」的筆記到「音浴」、聲響的空間,觸覺與言語之間的關聯,觸與語言的轉換,好像在這些不那麼緊湊的言說中,留出一些可能性。閱讀過程中,我常覺得是我不夠聰明嗎?無法捕捉到作者想要表達什麼中心思想究竟是什麼?可是有時候又覺得自己好像能夠對這些文字產生某些感觸和體會,給自己帶來某些東西。我常在這兩種狀態中徘徊。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鷲田清一也回應到了這點,他說:「有一種說法叫『過剩的理性主義』。那是指一種態度、一種心性。過剩理性主義者執拗地堅持,對話中的話語及其所表達的意義內容,必須有邏輯的一貫性。他們無法容忍對話時話題被岔開,受不了隨口胡謅的內容、前後矛盾的主張、缺乏結論,或是對話中有任何曖昧、空白,比方說話的人吞吞吐吐、夾雜著沈默等等⋯⋯(176頁)」若放到讀者和作者的關係來看的話,讀者也並非是單純的以被動的姿態在理解著作者的話語,要去抓住作者究竟是怎麼在說的,他的邏輯、推理究竟是如何的,是不是言之成理,等等。這讓我想到有些時候學術的寫作中,某種嚴肅、嚴謹、講求邏輯的生冷硬的氛圍,這樣的知識如何與外部交流,如何與他者相遇呢?
就「聲音送達」來說,「碰」和「觸」的狀態不太一樣。
鷲田清一用了<廚房的聲音>這篇小說,來描繪聲音如何「碰」到我們。在片段中看到阿秋和佐吉兩夫妻,兩人本來一同經營小料理店,某天佐吉病倒了,醫生告訴阿秋佐吉的病要治好很難,阿秋沒有告訴佐吉病情的事,自己操持著料理店,維持著原本的樣子。某天佐吉說起阿秋做菜,他聽到阿秋做菜的聲音「變小」、「聽起來不太清爽」、「有時候那聲音就好像躲著婆婆的小媳婦一樣」,阿秋不知道佐吉在說什麼,以為是他在變相得說她做菜不好等等。佐吉所謂的阿秋做菜的聲音變小、躲著什麼,其實是阿秋擔心聲音打擾佐吉而努力抑制,「試圖消去聲音的表情(182頁)」,但即便如此,佐吉還是聽到了聲音中細小的變化,並且也讓他在意。「阿秋害怕心裡想的事(佐吉的病情)傳達出去,不願走到聲音的另一邊;佐吉則被聲音的斜面勾住,跨不過去。(183頁)」鷲田清一對聲音的傳遞的描繪很立體,他說:「聲音在他們兩人之間築起一道牆,這道牆反射、映照出他們各自的意識(183頁)」,聲音雖然發出,但是未必會送達,「……有時候聲音也會以『碰』的方式送達對方。『碰』並不是根源性的事件,不會像『觸』那樣改變主/客關係。無需贅言,當我們在『碰』的行為中仔細碰觸觀察對象的表面、或是對其內部進行觸診的時候,碰觸者與被碰觸者經常是分離的。(183頁)」
鷲田清一以梅洛-龐蒂的思考「感覺的反射性」——看見與被看見、碰觸與被碰觸的可逆性,正是如此,聲音才能送達特定某人。「話語是他者存在的肌理(186頁)」,話語構成了在「我」與他者相互碰觸的介面⋯⋯「『聆聽他者聲音』這件事的根源,是觸及『超越自/他、主動/被動等區別,也就是相互滲透的場所』的經驗。在這種經驗中,我們接觸到他者聲音的異質性——不同的聲音表面(觸感),不同的體溫——而這樣的接觸,讓我們確實回到自我存在的根源。這樣的過程不斷在我與他者之間反覆發生。而缺乏這種與異質事物的接觸,經常是心神錯亂的原因(187-188頁)。」聆聽他者的聲音關乎觸與被觸,「聲音的皮膚」的被製造、強化⋯⋯書寫至此,我想到經歷嚴重創傷的主體的難以發聲、消聲,經歷極度痛苦的創傷的人,是失去座標的人,同樣的,也完全失去聆聽位置的、懸浮的人,那裡是,你想像不到有一個怎樣的他者,那裡是他者消失,所以「我」也就消失了的地方,「我」發不出聲。所以聆聽更是尤為重要,倘若沒有聆聽的耳朵,自我會面臨崩解。皮膚是身體內外交界的地方,如同在自傷的案例中可能會遇到的狀況,用劃開皮膚,造成疼痛,來體驗內心的痛。假如外顯的傷口成為探知內在痛苦的線索的話。聲音,這個人與人交流的交界面,對於失去了「我」的聲音的創傷主體,沈默或失語的存在肌理,可以如何被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