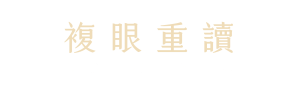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吳明鴻(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候選人)
當論及「照顧」和「療癒」議題時,身體性(corporeality)無疑是一個必須被重視的界面。人透過身體與外在環境連通,它生產出十分具體的知覺(perception)和感覺(feeling),一點也不抽象,而我們的存有也時刻架接在這些身心覺受之上。儘管,我們有可能忽視它,卻無法否認它,因為就算否認也沒有用,它總會一直存在:一部份以一種可感的對象物存在,另一部份又還黏附於身體本體的層次。
我認為,身體的這種具體性以及它「幻化生成」的能力(余德慧 2018),在這個人類心/身充滿憂鬱和焦慮的時代,以及各類身體修行與智慧傳統各立山頭的時局中,特別值得被認識與開發。本文將分為兩篇(即「身體—物質的精神生產」的「之一」與「之二」),各透過一個案例來探討關於身體幾個面向:銜接(articulation)、創造在己差異(difference in-itself)以及使主體獲得領悟(inspiration)的潛在路徑。這兩個例子分別涉及「悲傷」的心理狀態以及「運動」中的精神性生產。
進入案例的介紹前,以下先提出幾個發問,它們作為本文的指引,幫助我獲得一個閱讀文本作品和身體經驗的角度。這些問題包括:一、身體如何與外界連通(一個關乎「銜接點」與「銜接方式」的問題)?二、身體能做什麼(「功能」與「效用」問題)?三、身體的界限如何延展,延展後的「身體」的意涵又該如何認識(身體變形(metamorphosis)的問題)?四、物質世界與大自然又如何透過身體的感應力而將其「運送」至他處(elsewhere)(「物性」的課題)?五、身體在怎樣的運作下進行精神性生產(身體—精神的問題)?

美國知名心理學家羅門尼遜(Robert Romanyshyn)曾經歷喪妻之慟,《哀慟的靈魂:愛、死亡和轉化》(The Soul in Grief: Love, Death and Transformation(Romanyshyn 1999)一書就是他的悲傷之書,以兩百多頁的篇幅,書寫他喪親後七年間的心路歷程。在此,我們很容易透過無論是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物質想像」、榮格(Carl Jung)的「集體無意識」,抑或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杜伊諾哀歌》等思想資源,來認識這本書藉由談論哀傷如何深入了一個無意識的探索旅程。然而對我來說,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它揭示了:一個喪偶之後被悲傷淹沒、行屍走肉的中年男人,步上了一條與白日世界迥異的「幽冥黯路」,後者卻是全然身體性的,因而顯得無比的真實;它既非想像,亦非隱喻。以下,將透過本書的兩個片段加以詮釋。
在妻子過世後的一週年紀念日,羅門尼遜手執天堂鳥和鳶尾花來到了海邊。過去一整年的自我封閉,使他十分渴望與這個世界重新接觸,然而難過的是,他意識到自己已成了「鬼魂」,與他人之間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而「一個鬼魂又如何被他人所看到或聽到呢?」他這樣說道(Romanyshyn,1999: 41)。然後,他開始向大海拋擲出一枝枝天堂鳥花,這個動作彷彿是自動化的、被大海所導引出來的。那時的浪非常的大,花朵隨之被拍打、激盪、很快的漂流而去,在海面上時隱時現,作家以目光凝望,此時他開始感到有些異樣感,他說,自己「感到靈魂的某物可以棲息在花朵上」。
可以想像,親人遽逝使他來不及哀慟,就被日夢(day dream)的薄膜所包裹,過著與世界相隔離的破碎時間;但現在,大海的強力突穿了他,不但以聲響和洶湧攫獲了他,更讓他感受到了一份生命的快速脈動感,他開始有「一種小小希望的奔騰」在醞釀著。接著,一個奇蹟發生了:他目睹四散的花束被海流帶向遠方,不斷遭到衝擊,被帶往目光所及的最遠的海平線,他緊盯著這一切,完全無法鬆懈,一同進入了這險象環生和消殞災厄的命運之流中。此時,一個十分清晰的感覺浮現了——「我力不能及」(即:自己再也無法收回這些拋擲出花朵,一種筋疲力竭感),但隨即,下一個念頭又升起,給出了有如電影蒙太奇(montage)手法般的臨接(adjacency)與併置(juxtaposition)效果:「如果我持續夠久,也許可以被我的雙手緊握」。
但「持續」什麼?「緊握」什麼呢?而所謂的「蒙太奇」又是指涉何種拼貼呢?原來,這句話指涉的是一年前的那個事件:那天一如往常,他的太太在傍晚時分推開家門,卻在離先生不到幾公尺遠的玄關處,突然倒下,下一刻就因心肌梗塞猝然離世,羅門尼遜目睹了這一切。彼時,兩人僅隔著一個帷幕的距離——這就是「問題」的所在,這也因此生產出作家日後千次萬次的芻思與懸念。所謂的「問題」是這樣的:那時與妻子間物理距離上接近性,和下一刻的「生死兩相隔」所導致的觸及的不可能性,兩者之間,形成一種決絕而荒謬的隱喻性對立,而這種「近」和「遠」之間弔詭性,讓羅門尼遜此後的日子時不時就要揣想:那時,就在那個時刻,我原本有可能挽回嗎?有什麼是我可以更早覺察的?每一個可能的線索,被一次次地毯式搜尋,以致面目已然模糊,哀傷主體依然不願放手。
在這個場景中,哀傷主體的問題性遭遇了大海巨大量體的解構動力,儘管很快的,這種被捲入、難以區分的狀態在下一刻就煙消雲散了:海洋和日光成為被他厭惡痛恨的事物。然而,剛剛經歷的仍是一個紮紮實實的身體事件。我們幾乎在本書的每一頁都讀到這樣的事件性,多到讓我們渾然不覺,恍惚間跟隨作者遁入一個「底世界」,一個萬物有靈論(animism)世界的脈動裡:與動物園悲傷的大猩猩締結關係;感受到光暈中天使的溫暖與柔和;進入綠色植物本體的生長韻律;成為土壤過程中的碎裂碾壓感;與非洲大草原野生動物的相互凝望時刻;在暴風雪中瘋狂地向山頂駛去只為了向宇宙間不可見的巨大力量宣戰表達憤怒……。
這並不尋常。如果沒有受到召喚,大海怎能「拉走」羅門尼遜手上的花?如果沒有身體的開放,這個乾涸枯槁的遊魂怎能進入驚濤駭浪,進而體驗這情急、粗暴與狂野的動態意識?在此,「身體—物質」的「寄寓」的特性十分顯著:靈魂—花朵,心—海洋。其後,「遠」的質性(quality)對哀傷男人顯現為「身體所不能及」的身體意涵,以及隨之而來的焦急感、畏懼毀滅和筋疲力盡的無力感受,殊不知,下一個乍然到來的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卻直接置入與男人過往的精神創傷相併置/連結的感覺(一個時空:妻子驟逝的那個傍晚的玄關處):原先的「身體—遠—難以企及」被疊加以「堅持—遠—或可觸及」新意念:一個帶出了「希望」的身體流變,主體在「身」中伸出了「意念之手」去緊握那永恆的失落。這不可能的希望/希望的不可能性是一個致命的傷痛,然而經由大海帶出的事件性,再一次啟動了關於希望和失落的身體性操演(perform)。

我們知道,喪親的哀傷時常是「無路可走」的:它們通常不是已可被表徵(represent)、進入了象徵符號界、可被談論的過往記憶,而是還黏附於肉身、以盤桓不去的、糾纏的、暗影式回返的方式,困擾著主體,主體付之以芻思或陷入日夢,卻無法掌握攫抓,無法談論或賦予意義——在這個本體的意義上,羅門尼遜依然置身於喪親事件中,無法將之客體化(objectify),於是嚴格說來,他也不曾真的「離開」事件當下的時間點,但現實卻是,他再也「回不去」那個時刻,他的確是被卡在「之間」(in- between)。「靈魂」因而無所依止,對現世的感覺會被塵封,原本支撐主體存在於世的意義的星圖(constellations)也受到了根本的動搖。於是乎,世界繼續轉動,而主體卻自此冰凍、封存。
正是在這一點上,身體做為「連通道」,卻能透過異樣的連結,驅動另類的意義化、新象徵物的可能。我並非意欲透過這個論點,將哀傷療癒的歷程說得過於輕易,因為這必然是虛假的。本文的用意僅在於凸顯:身體的銜接和生產能耐可能超乎想像,而身體感覺的精神生產亦可能超出預期,特別是相較於悲傷情緒的凝、滯、鬱、結,自然界流動和各種偶遇中的力量、強度、密度、濃稠度、深度等可感質性所可能打開的主體空間,值得進一步探究。案例中的「大海」作為一個主體寄寓其上的「半物」(王心運,2006),其物質力量表現性、衝擊性及流動性使得身體成為了連通管道——哀傷主體(及其意識、語言、認知)的「無能」與受觸動身體(affected body)幻化生成的「大能」,剛好形成鮮明的反差,兩者間進行著激烈交流,一同走向未知。
余德慧(2018)從修行的觀點,將這個身體被開啟的狀態稱為「物的空間」,也注意它和日常生活中許多微小的感官事件的相通,以「喝熱豆漿的感受」為例子,「有熱度、能量、力道、味道,以及看得見的冒煙」,這就是「如實」的意涵。物的空間就是力量的空間,力量本身是一個「絕對值」,一個絕對的「差異」,「就好像一個石頭打在你頭上,力道是多少,你就痛得多深刻」(余德慧,2018:341-342)。如此簡單而直接。
再透過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概念(Deleuze 1980[2010]),我們將能走得更遠。無器官的身體並非一個形上學的概念,相反的,它絕對是真實的,它就是慾望(desire)自身,是慾望所能及的限度,也是人類身體可能的延展、連結和流變。這個概念拒絕「組織化的身體」和「功能分化的器官」,而著重一種「渾體」的反應和動態,以及個體身體與外在環境碰觸中所產生的「外部關係」——一種非關係(non-relation):此關係的屬性並非預先被雙方所設定;個體的既定屬性(一種「組織化」的框架)並非此關係的先在條件,而是相反:該遭逢所迸發出的非預期流變現象,才反過來決定了作為網絡狀(networked)無器官身體一部份的個體的當下意義。若我們想起羅門尼遜的身體—大海,以及稍後討論的身體—植物、身體—礦物等,將可認識到這是一個無法區分(indiscernible)的流變地帶。而悲傷者的慾望要流動,一個重要的敲門磚就在於身體的感知和感覺。身體成為一種「武器」,不但得以變形,銜接外部,亦能銜接出網絡關係裡的巨大能量,以構作此前不為人知的存有狀態。
讓我們想像一個場景:羅門尼遜長時間躺在黑暗中,身陷客廳沙發裡無法自拔,他無法起身,也不願起身,生命際遇令他無比悲哀,因而進入到關於「蟲、岩石與天使」的「物質想像」裡(Romanyshyn 1999: 62-71)。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哀傷男人的敘述中,「想像」二字原先屬主觀意識「虛」構的意味,幾乎被身體感覺的「實」給完全驅散了。擁有許許多多的動詞和感受性,是這個作品的文字特徵:撕成碎片的身體、粉碎、混入、壓、睡、韻律、重擊、掉落、無限的向地底深入沉入,連夜晚的「黑」也有「冷峻」的質性。羅門尼遜的身體「迷失在綠的緩慢韻律」中,意指他的靈魂的「慢」的狀態有別於世界的速度;而外頭的雪,「包覆我的植物靈柩」,他化身為植物,沉浸在植物的韻律中(他需要另一種韻律、速度和生長運動方式,來支撐起悲傷的身體)而被「封存」於靈柩中,且「包覆」以冰冷的雪。
作者「在植物的沉睡中深深的休憩著」,對時間失去知覺,卻有一位深沉的「礦物巫師的看顧」,這個被凝視的視覺感受無疑是一種保護。肉身已然變形,他深深休憩,而誰又是礦物巫師?不知,但他象徵著他的未來,是綠色植物腐爛後的歸止處,具更緩慢的時間韻律,並化做另一種存在樣態,在腐爛的過程中將接受無數無名昆蟲的啃噬。接著,還有那土壤層堆的「重壓感」,礦物巫師繼續兀自站在那邊,以他的韻律,以他的看顧。植物化做碎石了,而「(植物的)綠色(生命)只是礦物之夢?」此時,礦物存在的質性是清晰的,「只是形狀與紋理,以及易碎而堅硬的堅持著的察覺」。既大海之後,礦物巫師是下一個幻化為讓身體既沒入其中、又作為外在世界之對象物(object)的存有。
這些關乎「哀傷的韻律」的書寫教我們探問:對於哀傷之人,怎樣的物質感受可以呼應這種向地底沉入的棄絕生命的姿態?他能被允許以怎樣的速度存在於世?若將人世間的話語、思考和理性與石頭、植物和大海等物質界萬象相比,觀察它們各自與身體的銜接狀況,則這則「礦物之夢」的非人的、物理的質性,是否更能承接那悲哀的身體呢?
羅門尼遜認為這是一個「成孤」(become orphan)的旅程,一次飄盪之旅,有時,作者偶遇黎明晨星的點亮,偶有大自然的天啟和萬物的慷慨賜予;另一些時候,則恍若魑魅魍魎俱在其中,不知此等哀傷將流溢至何時方得干休,然而,一切不是處處無光的慘澹無望,相反的是處處閃爍著幽光——當身體和情緒掉落瓦解到了一個低谷,這幽光才溫潤得了人心,開啟了身體疆界崩解和無邊的物質想像。羅門尼遜用他細膩的筆和蜿蜒盤繞幽暗邊緣的文字,寫的雖是人世間悲傷幽谷,卻成就一本有著濃濃宇宙氤氳之氣的書。
在羅門尼遜「成孤」的過程中,體現的正是一種影響和被影響(affect and affected)的關係,或說是身體和外在力量之間的潛在關係。德勒茲的情動(affect)概念探討的就是這樣的力的本體論世界,而哀傷也需要回到這個力的本體論,回到一個身體—物的銜接空間去做分析。這裡頭,生命透過「觸」之「知」(touching-knowing)獲得了事物的反餽,而這種「觸」的經驗,也成了喪親者重要生命啟發的門徑、源頭。
如何運用身體感知和感覺,以其做為通道,和外在世界的各種機遇與介質相連,以其中的流動性和質性去啟發並操演可能的精神生產,以獲得生命的動態、變異與轉圜的可能,是一切的奧秘所在。
Romanyshyn, Robert. (1999). The Soul in Grief: Love, Death and Transformation. California: Frog Ltd.
王心運(2006)。〈身體與處境-赫曼•許密茲(Hermann Schmitz)的新現象學簡介〉。《哲學與文化》33卷2期,頁83-99。
余德慧(2018)。《生命轉化的技藝學》。台北:心靈工坊。
姜宇輝(譯)(2010)。《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卷2 千高原》。上海:上海書店。(Gilles Deleuze,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