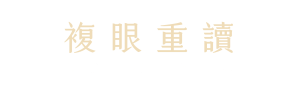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黃奕偉(政治大學宗教所博士)
聽見上帝的聲音?
周日的午後,教會一位媽媽說到自己的女兒,大概是小學中年級的年紀,參加主日學後,回家問她說:「為什麼老師講的聖經故事裡,神對亞伯拉罕說話、對摩西說話、對撒母耳說話,有那麼多人聽過神對他們說話,但我卻從來沒聽過上帝的聲音呢?」媽媽的表情看起來有些哭笑不得,在場的老師與牧師也一時語塞,雖說是童言童語,小女孩的疑問卻是直指核心,在這個科學理性的時代,還會有「正常人」會聽見上帝的聲音嗎?
2018年6月至2019年8月,Cook等人(2022)在Church Times這個基督教的網站與紙本刊物上刊登廣告,邀請曾聽到過「具有靈性意涵聲音(spiritually significant voices)」的讀者來參與這個調查。在問卷的簡介中,他們並列了「聽到聲音」、「聽到或感受到上帝、天使、聖人、惡魔或其他靈體的存在」等現象,也說明了問卷目標是希望更多的理解這樣的經驗,最後收到58份完整的回覆,這些調查參與者的主要人口學特徵是:主要來自英國(97%),大部分是女性(71%),大多數年齡在 45歲以上(86%),此外,大部分受訪者都未曾有過任何精神疾病史(76%)。對比Church Times每周有兩萬份的紙本印刷量,以及超過兩萬六千次的網站瀏覽數,56份的回覆報告顯然是相對稀少,但我們卻也可以在這樣的調查中知道:這樣的經驗確實存在,並且,不一定得要與精神疾病的幻聽(auditory hallucinations)直接畫上等號。
不只是幻聽
對聽覺的生理性理解常是從聲波傳導的生理結構層面談起。聲音需要透過介質來傳導,無論是空氣、水或是固體,都藉著震動帶來的連續觸碰來傳遞聲波。聲波經由外耳收集後,震動鼓膜,再進到中耳的三小聽骨來到內耳的前庭與半規管,以及耳蝸,在耳蝸內觸動毛細胞轉為神經衝動,再通過聽神經傳遞至大腦皮質中,對聲音的聽覺於此而生。但從這樣的角度來看,也就是從感覺歷程的觀點來想,關於聽見神說話的現象,就常會被認定為是一種幻覺。
就定義而言,幻覺指的是「對於不存在現實世界之事物的知覺」,也就是看見或聽見不存在的事物(楊玉齡譯,2014:6)。在當中,聽幻覺(auditory hallucinations)是相當常見的經驗類型,被認為既是多種心理疾患共有的症狀,卻也常在沒有精神病史的人身上出現。以Woods等人(2015)的研究來說,他們通過醫療網絡、病友團體與心理健康論壇來刊登廣告與發送連結,以網路問卷方式調查,在153份自陳有過幻聽經驗者的回覆中,就有17%的人未曾有過任何精神病史。
除了不僅是幻覺,對非現實事物的感知經驗,更可能是種意義深遠的靈性體驗。進一步深究聽見「具有靈性意涵的聲音」,究竟聽到什麼?就現象層面而言,Cook等人(2022)將這樣的經驗感知形式分類為:單純聲音(52%)、單純思想(24%)、思想與聲音混合(21%),並且也指出合併身體感受的幻聽類型所佔的比例也不少(26%)。從聲音的來源來區分,有88%認定其來源是神聖的,並有2%認為來自於魔鬼。再就聲音的內容而言,則可以分類為安慰、呼召、確認、改宗、溝通、危機、對話式的、陪伴與其他(Cook et al. , 2022)。
這些聽覺經驗,對當事人而言,可能在不同層面都有其特殊意義,或許與個人身分認定有關,也可能與所屬群體有關,甚至能提供特殊的意義感(Cook et al. , 2022)。很顯然,對聲音的感知同時涉及對聲音的理解,對聲音的主觀詮釋也是整體聽覺經驗的必要成分,不過這會將討論範圍跨出目前的感知主題,延伸到理解的認知歷程上,我們姑且先擱下,暫時聚焦在聽這件事。
耳朵是最重要的宗教感官
關於聽見上帝的聲音,或說聽見「具有靈性意涵的聲音」,這當中的「聽」究竟是怎麼回事?就如普呂瑟(Paul Pruyser)所指出的,在所有宗教有關的聲響中,最重要,或說最為神聖的,莫過於言說。而這對於基督宗教而言,尤其是如此。約翰福音開宗明義就說了:「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神聖的言說本身,即是神的具現。與言說相應的聆聽,其重要性自然也不容輕忽,就如保羅強調信道是從聽道來(羅馬書10:17),當神的臨在即是神聖言說的臨在,那顯然必需要通過耳朵來聆聽。縱使不局限於言說,聲音與聆聽仍是各種崇拜儀式的底景,耳朵被視為最重要的宗教感官,似乎並不誇張(宋文里譯,2014:90-92)。反過來說,聽不到就嚴重了。absurdity(荒謬愚蠢)這個英文字的拉丁文字源來自surdus,指的是聾(deaf)。與視覺、嗅覺或肢體的失能相比,聽不到所遺漏的線索,可能使世界缺乏意義,理解也隨之片段、甚至錯謬(莊安祺譯,1993:166),海倫凱勒或許最有資格對此做出評論:
我聾的程度就和我瞎的程度一樣,失聰的問題比失明更嚴重、更複雜。失聰是更糟的不幸,因為它代表喪失了更重要的刺激—喪失了創造語言,使思緒奔騰,使我們與人類智慧相伴的聲音。…我發現聾比盲是更大的障礙。(引自莊安祺譯,1993:181)
聽的現象學描述
但我們如何能夠真實聽見這些「幻聽」經驗者的聲音?如何能夠不只停留於醒目的非常態現象,而更能關切於其作為置身現場之當事人所經驗到的?通過具體的案例,以及鷲田清一關於聆聽的現象學描述,也許能幫助我們暫時將「幻」懸置,如實回到「聽」之中。
以現象學方法來對「聽」做出描述會有什麼不同?鷲田清一曾藉著我們每天都經驗到的目光交會現象來勾勒出現象學描述與客觀分析的差異。日常的目光交會是怎麼回事?當我跟你眼神對上,相互注視時,目光既被吸引,卻又同時想要移開,雙方的視線既同步卻又相互屏蔽,這樣的現象如何能夠理解?如果對比我們盯著假人或凝視著維妙維肖的蠟像,看著它眼中兩顆黑色珠子,我的視線卻可以霸道壟斷整個注視經驗,兩者的差異顯然不僅是視覺生理上的不同,更牽涉到正在看的我也同時在注視經驗中無可遮掩地暴露自身。然而,分析性的討論,是讓自己立足於「看」這個事件以外的第三者位置,但看總在實際的生活世界中發生,抽離於這個場所,立足於某種數量式的抽象空間,顯然無法描述有一道視線與我的視線交會這樣的經驗(林暉鈞譯,2022)。
對聽的討論也同樣需要回到生活世界。我們都曾經驗過旁人大聲叫喚,我們卻充耳不聞的狀態;也曾在嘈雜的街道中,確實聽見呼喊我們名字的細微聲音穿過人群。在兩個情境下,聲波同樣通過空氣傳導了,外耳也確實將振動收集到鼓膜往中耳傳遞了,但接收結果為何卻大不相同?關於「他者對我說話」、「我聽到他者的聲音」這樣的感知,究竟從何而來?

往超越他者調校的運動意向性
鷲田清一認為,他者的聲音之所以能夠傳達,是因為身體的整體運動意向性朝向、觸及對方,而這也要求自我與他者的身體必須共在於共同的生活世界與運動空間之中,運動意向性才能夠交會;反過來說,當自我認為他者是客觀空間的東西,僅著眼於數算距離、量測頻率與次數、刻意調節聲量,那聲音反而無法傳達(林暉鈞譯,2022)。過度用力發話造成壓迫甚至封閉對話空間,害怕沉默於是說個不停,種種都讓說話成為無法抵達他者的聲音。
Luhrmann(2006)民族誌中的例子,就描述了將運動意向性逐步往超越他者校準的過程。N女士年幼是在改革宗教會,二十多歲時隨著丈夫轉到天主教會,那時她認為神是抽象而遙遠的,直到四十多歲時,她開始尋求更深刻的宗教體驗。那時她開始早起嘗試讀聖經,經過幾周的閱讀之後,她感覺到有一個聲音喚醒了她,那聲音很明確是從她、從她的頭腦之外被接收到,然後她聽到那聲音說:「讀雅各書(Read James)」回想起來,她說:直到那天她才知道雅各是聖經中的一本書(Luhrmann, 2006:150)。
N女士的例子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中世紀教父奧古斯丁在《懺悔錄》第八卷中所記下的親身經驗。奧古斯丁那時在屋內因著自己的罪惡掙扎哭泣,卻聽見從鄰近屋中傳來的聲音,他不知道那是來自於男孩或女孩,只能確定那是一段歌詞,反覆唱著:「拿起來讀,拿起來讀(Take and read)」那時他停止哭泣,只是專注思索著是否曾聽過有孩子在遊戲中唱到這樣的歌詞,但卻記不得曾經聽過。他很確定那是來自於神的命令,要他打開聖經閱讀。於是他走去拿起聖經,打開後就讀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馬書13:13-14)。」(徐蕾譯,2007)
在N女士與奧古斯丁的例子中,有幾個有趣的共通之處。其一是他們在聽到神的聲音之前,都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與尋求。N女士自發性的晨起讀經,奧古斯丁則是反覆掙扎於情慾與基督宗教信仰之間,經過長時間的探索,他緩慢地將自己區別於占星、摩尼教等當時的異教事物,這個逐步調校的過程目的都在於將身體的運動意向性逐步朝向,以觸及超越他者。
而在將運動意向性逐步指向超越他者之後,N女士與奧古斯丁都接收到讀經的指示。Luhrmann沒有提到N女士在雅各書中得到的啟示,而更多關注她在後續如何在禱告中獲得更多的圖像與語言。奧古斯丁讀到羅馬書的那一段話之後,他意象式地寫下自己如同被一道光徹底照射到心中的每個角落,內心不確定的黑暗也一掃而空。之後他將事情經過告訴他的朋友阿利比烏斯,阿利比烏斯請奧古斯丁指給他看剛剛所讀的經文,阿利比烏斯也讀了,並且接著讀下去,然後自己在緊接著的下一句經文中得到對他個人的指引(徐蕾譯,2007)。
聽的特定性與時間感
對運動意向性的模塑,不僅在禱告的操練中,也在關於讀經的教導中,這不僅發生在奧古斯丁與他的朋友身上,在N女士及葡萄園教會群體也是如此。對葡萄園教會的信徒來說,聖經並非是用來記誦的文本,而是一份專屬於每個人的私人文件。正如B先生所提到的:「我連續去了(教會)幾個禮拜,我聽到聖經,聖經對我講話,它對我個人說話……這是一個愛情故事,並且是特別寫給我的(Luhrmann, 2006:146)。」閱讀已經寫下的文字,與聆聽正說出口的話語之間,直接的差別就是讀者與聽者的不同,讀者是一般性的普遍對象,而聽者卻是說話脈絡中的特定對象。將聖經當作私人文件的教導,就將信仰者從脫離書寫者脈絡的非特定讀者,校準為指向明確超越他者,置身於個人生活世界的特定聽者。當聖經中的每句話都是專為我而寫下,是神對我發話,作為聆聽與對話的禱告才能夠體現出來。
聽與讀的第二個差別是時間。書寫的文本是已然寫成,全盤托出的;說話則總是在已經說出的、與想說的之間有著時間落差。聽別人說話時,聽者總是意向於對方想說的話,而不只停留在已說出的話,其理解總是預期並等待未說的話來得到整全,時間的落差就會帶來理解的總是未完成。也因此,對鷲田清一來說,發話與聆聽之間就會有timing的問題,很顯然,這樣的時間並非是客觀數量化的時間,而是在事情中的時間,是在說與聽之間的間距。
關於timing或間距的現象,或許從反面的經驗比較容易理解。我們可能都曾遇過對話雙方同時說話,互相堵住話頭的場景,於是兩人必須互相禮讓(你先說!)以核對誰來重新開啟下一輪對話。對話過程中的一來一往,也就是對話輪替(conversation turn),實際上是語言發展的必經歷程,兒童必須從觀察並掌握說話與接話的間距中體會。當抓不準timing、無法取出合適間距時,人常會更快更急地說更多的話來填補間隙,以避免令人不快的沉默,但如此出現的話語卻往往讓兩人的距離更遠,雙方反而更不容易真正接觸(林暉鈞譯,2022)。

在互動關係中體會timing
但就如同鷲田清一所觀察到的,所謂合適的間距、或對話雙方在timing的一致與分歧很難用語言清楚表述,因為其本質是一種身體部署,或者像是工匠的身體記憶/技藝,這中間的差異或許可以類比於閱讀駕駛操作手冊與實際開車上路的不同。於是我們只能透過互動與關係來體會,以鷲田清一的話來說,那會是需要透過某人的「道成肉身」、或是透過「彼此同步的相互呼應」,來進行身體技藝的傳承(林暉鈞譯,2022:98-99)。
這也再次提醒我們,朝向超越他者的運動意向性,與個人所屬群體、特別是代禱群體的關係密不可分。在奧古斯丁的經驗中,就如前面所提過的,他自己知道受到啟示,就跟一旁的阿利比烏斯分享,阿利比烏斯也讀了,並且也在下一節經文中同樣得到啟示。群體間的相互印證,不僅僅是一種社會性的增強,他們也在彼此模塑出越發精準的運動意向性。除此之外,我們也不能忽略奧古斯丁母親莫妮卡的重大影響。在《懺悔錄》第六卷中,奧古斯丁寫下他的母親莫妮卡堅定的信心和熱切的愛心,她為奧古斯丁的受苦流淚禱告,也堅信在她行將就木之前,奧古斯丁必然會皈信天主。莫妮卡以堅定為孩子祈禱而聞名,她的代禱與眼淚就親身示範,並且也在禱告中形塑了奧古斯丁朝向超越他者的運動意向性。
timing是作為事情的時間
葡萄園教會對於禱告與讀經的集體操演,在Luhrmann的描述中已經可以見到,禱告的間距由「對神說話」、「等候神」、相互核對意識浮現的話語或圖像這幾個步驟所構成,而這當中難以言說的timing就在不同的事件中浮現出來。
N女士關於代禱的例子某種程度可以呈現出如何體會timing的蛛絲馬跡。N女士在加入葡萄園教會後發現自己很有禱告的恩賜,而這特別凸顯在為別人代禱的事工中。N女士說自己剛開始時並不知道怎麼禱告,她感覺自己與上帝沒有連結,於是她開始觀察其他會眾,聽他們談論如何與上帝建立關係和信靠上帝,而在開始學習一起為別人禱告時,她說到:「直到我開始參與代禱事工,我才真正感覺到有所突破。」所謂突破指的是,她開始獲得一些她確信是來自於神的圖像或話語(Luhrmann, 2006:150)。
每年有一段時間葡萄園教會都會號召會友一起為當年度的全國性會議禱告。N女士非常看重這個工作,每天早上為此禱告。在某一天早上禱告後,她心裡浮現一個圖像,她以為自己是分心了,但卻還是一直看到船。還在想著那些船時,電話響了,是牧師打來的,他們談了一些事,告一段落後,N女士說自己等待,然後有一股感動,讓她問牧師說:你為什麼打電話給我?牧師回答: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覺得我應該打給你。接著,N女士突然意會到,看到那些船並不是因為她禱告分心,而是與禱告有關。於是她告訴牧師關於船的圖像。隔不久見面時,牧師告訴N女士,有好幾個人都看到相同的圖像,原來是耶穌把手放在船舵上!N女士說:「你知道,這聽起來很瘋狂。但它就是這樣運作的(Luhrmann, 2006:151)。」
從對神說話、等候神、到話語與意象的浮現就客觀時間而言,間距是不等的,沒辦法以計時器量度每個步驟應該在多少時間完成,又應該靜置多久讓其發酵。但我們確實可以觀察到這樣的timing是作為事情的時間,是現實事件影響人的時間。N女士在每日的投入代禱之後,她等待,那聲音或圖像有時出現,有時沒有,甚至出現時,也不盡然直接可以把握,然後她等待機會將這些外來的訊息在代禱群體中陳列出來,相互核對,或許會在拼圖湊齊之後,那個完整的圖像才會浮現。關於聽見神聲音的timing,或許就像在這一連串從說話到等候,類似拼圖的個人行動之中,一點一點摸索出全貌,而在整個禱告行動的底部,穿透、貫串整個事情的是那個被模塑出的、穩定朝向超越他者的運動意向性。

聆聽他者的聲音
從朝向超越他者的運動意向性、作為聆聽的禱告中由向神說話、等候神、拼湊圖像所構成的timing,以及代禱群體中彼此同步相互呼應,我初步描述了聽見上帝聲音的「聽」,所可能需要的幾個構成部件。信仰者在摸索、聆聽神發話的timing中,型塑生活的節奏、模塑指向神的運動意向性以及由此組構出的禱告身體,timing,就如鷲田清一所說的,成為「互為主體的介面現象(林暉鈞譯,2022:97)」也體現出自我與超越他者的互動關係。在摸索時間性的timing以及空間性的間距時,作為信仰者的自我將自己託付在聽與說之間,鬆開自己的框架、感受他者,讓自己在間距中被動搖、搓揉、甚至有著在聆聽中得到新型態自我的可能性(林暉鈞譯,2022:99)。
那麼,繞了這一大圈,針對小女孩的提問,我們究竟有什麼可說?或許,那本來就不是以說來回應,而是要試著傾聽,「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不是嗎?那將帶來動搖、啟發與更新的他者,可能是某位未明的超越他者,但也或許,就是眼前的小女孩。
參考書目
宋文里譯(2014)。宗教的動力心理學。台北:聯經。(普呂瑟Paul Pruyser,1968)
林暉鈞譯(2022)。聆聽的力量:臨床哲學試論。台北:心靈工坊。(鷲田清一,1999)
徐蕾譯(2007)。懺悔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莊安祺譯(1993)。感官之旅。台北:時報。(艾克曼Diane Ackerman,1990)
楊玉齡譯(2014)。幻覺。台北:遠見天下文化。(薩克斯Olive Sacks,2012)
Cook, C. C. H., Powell, A., Alderson-Day, B., & Woods, A. (2022). Hearing spiritually significant voices: A phenomenological survey and taxonomy. Medical humanities, 48(3), 273–284.
Luhrmann, T.M. (2006). The Art of Hearing God: Absorption, Dissociatio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Spirituality. Spiritus: A Journal of Christian Spirituality, 5, 133 – 157.
Woods, A., Jones, N., Alderson-Day, B., Callard, F., & Fernyhough, C. (2015). Experiences of hearing voices: Analysis of a novel phenomenological survey. The Lancet Psychiatry, 2(4), 323–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