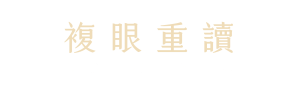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王鏡玲(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摘要
這篇文章我想探討兩位藝術家李錦繡(1953-2003)與柳依蘭(1966-)的人物畫 ,如何表現當代社會面對「神聖」(the sacred)的共同體–「家族」與「靈性」(spirituality)的變遷 。當我再三注視這兩位藝術家的人物畫之後,卻感受到剎那間、時間停格的心靈異質性的體悟。李錦繡與柳依蘭的人物畫所揭露的個人與家族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也正好是這個急遽變遷的社會,明顯的心理內在的變化,以及凝視生死奧秘的「靈性」層次。
李錦繡和柳依蘭的人物畫作品,讓觀者從視覺意象所凝縮的矛盾與曖昧的構圖氛圍(aura)裡,發掘到那藏匿在抽象與具體的「變形」圖像底下,所揭示的圖像意義衝突與對立的創作能量。這些透過藝術作品所透露的幽暗域外,和日常現實裡的理性界線或秩序,同時並存。藝術家穿越現實中源自生理女性、又超越壁壘分明的性別實存(existential)經驗、透過內在的獨特生命體驗的探索,進行著對所謂「客觀」和「普遍」的社會現實或禁忌、出其不意的透視。
0. 前言
這篇文章[1]我想探討兩位藝術家李錦繡(1953-2003)與柳依蘭(1966-)的人物畫[2],如何表現當代社會面對「神聖」(the sacred)的共同體–「家族」與「靈性」(spirituality)的變遷[3]。李錦繡跟柳依蘭的圖像在這個資訊爆炸、講求快速瀏覽的時代,變成一種一去不返、找不出時間去凝視的圖像鄉愁。凝視這些圖像的霎那,大數人在3C的手機或電腦小螢幕看到圖像時,只是一閃即逝,並非像我這種去展場或藝術家工作室仔細端詳的觀者。然而,當我再三注視這兩位藝術家的人物畫之後,卻感受到剎那間、時間停格的心靈異質性的體悟。這種視覺的經歷與反思,或許可以帶給觀者像打開了圖像意義的多重視窗一般。在這個凝視的視覺經驗當下,讓我觸碰到藝術家對於「人」認真且深刻的透視。
李錦繡與柳依蘭的人物畫所揭露的個人與家族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也正好是這個急遽變遷的社會,明顯的心理內在的變化,以及凝視生死奧秘的「靈性」層次。「神聖」(the sacred)是指人渴望「溝通」、追求信以為真的生命動力來源。「神聖」不只是指向特定宗教的「神」、上帝,而是同時包含被宗教人視為不同聖界分類的每一個具有靈力(或靈性)的主體。例如鬼魂、祖靈、動物靈、植物靈、物品、氣場、地球之外的能量體…等等,只要是宗教人所感受到對其身心靈,以及個體與集體命運產生影響的能量都包含在內[4]。
我稱之為「音容宛在」,指的是對於過往集體記憶中,正在消逝中,卻還依稀栩栩如生、信以為真、卻又必須面對消逝的認同轉變。在社會快速變遷、強勢歐美菁英文化長期影響之下的台灣藝術教育,生理女性菁英面對父系家族以及傳統靈性宇宙觀,在追求個人獨立自主的菁英教育影響下,產生怎樣的藝術表現,去折射出個人生命變化的存在感呢?藝術家的圖像所扮演與穿越的社會身分階級和時代縮影,又如何像是「音容宛在」共同體的餘暉,照耀在不斷快速奔向前的現實世界呢?
日本造型藝術家杉浦康平,曾指出,透過造型的感受,喚起我們尚未覺知的感官與悟性,感受到古往今來對造型的意義互相之間的照應。杉浦康平認為,「靈」(ち)是體內循環、自然界氣息與天地之間的靈力、信仰上的咒術魔力…等等,在「靈」的作用下,「形」變成有血有肉的「型」,產生蓬勃生機的搏動[5]。圖像造型都是從古到今,被數不清的無名藝術家透過創作,不斷重新融合轉化,成為今日我們所共同擁有的宇宙生命記憶的圖像[6]。這也是我所指的「神聖」顯現為圖像表現的意義[7]。
每一個生命與另一生命之間隔著一道鴻溝,這是獨立自主的人所感受到的孤獨感。原生家庭影響著每一個人,家族共同體不只是可見的家人,在漢人文化中,還包含對於父系血緣共同體的傳承與凝聚力。對於生理女性(以下簡稱女性)而言,她們所面臨的共同體歸屬,往往因為婚姻關係,包含原生家庭與伴侶(夫家)家庭,這些家族共同體關係不只是日常生活,還包含家族信仰與靈性上的關聯性。
隨著1960年代開始,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需求逐漸增多,菁英教育敞開的門,有更多女性進入職場,家庭結構改變、避孕藥的問世,改變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個人價值觀,以及生涯的展望[8]。女性受更高教育者越來越普及。在我個人之前通靈現象的研究[9]、以及本文將探討的李錦繡和柳依蘭的人物畫中,我看到了有自我意識的女性菁英,一方面想逃避和跳脫過去傳統倫理與宗教信仰權威、家族關係所塑造的自己,另一方面又面臨當前強調個人、疏離的社會關係中,人必須蛻變,重新去找到屬於這個時代自己的生命主體,與其他主體之間的溝通方式[10]。
李錦繡和柳依蘭的人物畫作品,讓觀者從視覺意象所凝縮的矛盾與曖昧的構圖氛圍(aura)裡,發掘到那藏匿在抽象與具體的「變形」圖像底下,所揭示的圖像意義衝突與對立的創作能量。這些透過藝術作品所透露的幽暗域外,和日常現實裡的理性界線或秩序,同時並存。這些視覺象徵意義的曖昧多義,宛如榮格(C.G. Jung)心理分析中,面對多重自我的對立並存關係(ambivalence)[11]。藝術家穿越現實中源自生理女性、又超越壁壘分明的性別實存(existential)經驗、透過內在的獨特生命體驗的探索,進行著對所謂「客觀」和「普遍」的社會現實或禁忌、出其不意的透視。
1. 李錦繡的「家族系列」
1.1 家族相片的負片透視
1960年代開始,台灣從傳統農業社會逐漸進入現代工商社會,人們也逐漸接受相機不再具有形而上的靈力,經濟力許可的家庭,家中成員使用相機來記錄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拍照逐漸成為家庭生活儀式的一環。從這時期起一方面相片取代了傳統肖像畫,成為祖先親族遺照最主要的媒材。另一方面,相片也成為那時代的年輕人,記錄那段青春歲月的重要見證物[12]。從1960年代到現在,幾乎變成人手一支的手機流行,拍照已經變成日常動作。但是李錦繡1980年初的「家族系列」,卻讓我們對於已經習以為常的家族照,有了另一種視覺的驚奇。

家族照片是現代社會中家族共同體記憶的視覺化,李錦繡在1976年到1980年代早期,將當時台灣學院內流行的美國攝影寫實,與她吸收李仲生(1912-1984)與培根(Francis Bacon,1909-1992)的抽象畫理念結合,以負片的形式,將家族照、團體照所見人物模糊、簡化,只留下剪影般存在的輪廓,這是那時期李錦繡的創作特色[13]。本文我所聚焦的李錦繡1982年「家族系列」作品,在人物圖像的留白處,加入血黑團塊,讓圖像充滿曖昧感與神秘性。

2008年我第一次在苗栗金枝藝術畫廊看到李錦繡的「家族系列」原作時怵目驚心[14]。剛凝視時的身體感受,先是雞皮疙瘩、有點冷的騷動感,有點像遇到「歹物仔」[15],但雞皮疙瘩之中,又有某種內在情感的溝通。畫作帶給我的不是劍拔弩張的挑釁,是親近、被剝開一般的逼視,被畫作逼視。「家族系列」所展現的畫面構圖,以人物畫的既模糊又形影可見,與紅黑團塊堆疊在人物之間的空間對比,讓我感受到內爆,而非外在衝撞。內爆是以滲透、黏稠、紅黑液體、排泄物或分泌物狀的蔓延,以這樣的「噁心」之姿,來模糊和人物群像之間記憶的界線,模糊被父權符碼體系所打造的家族共同體界線。但這裡的壓迫感卻帶有另一種曖昧的空間上的混沌,女體排泄物的兩面性,黏稠帶有生機,被父權文化視為污穢卻又是孕育家族的根源所在。

1.2 紅黑團塊
傳統女性在結婚之後,透過生育後代,來變換她的身分認同,從以原生家庭為主體的記憶,轉變成為以夫家為主、為人妻人母的家族記憶。傳統社會一位女性結婚之後,原生的家族記憶就被夫家的家族記憶取代了,她也必須成為夫家的記憶,最後變成祖媽[16]。
「家族系列」中的「家族」是原生家庭呢?還是伴侶/丈夫的家庭呢?家族人物形象的模糊與留白,以及家族形象前面的紅黑團塊,所產生的強烈突兀感,彷彿經血一般。這彷彿對於家族提出一直被忽略的根源–經血的記憶,貫穿家族的母血的記憶,或者是那些成為母,或者因無法成為母而死亡的過往祖媽們的痛呢?音容宛在的家族共同體,彷彿今生今世的牽扯、陰影,又彷彿古往今來生命源頭的因緣聚散因果糾結。這對於家族關係越來越疏遠、卻仍勉強維持的當代社會,「家族系列」一樣像先知發出令人震撼的圖像預言。
正如以下第二位要探討的藝術家柳依蘭,曾提到她自結婚後為了生育、傳宗接代進出醫院[17],每次她都認為生死關卡。這是生理女性在生育過程的生命考驗,承擔了一方面血脈相傳、另一方面經血不潔,這既沉重又貶抑的雙重標準。這種揭露心靈獨特的私密關係的圖像布局,在李錦繡的「家族系列」裡,所揭示的不只是以個人為出發點的「夢境」、「潛意識」的超現實意象,更深的關連應該是從「家族」、以及難以分離的人與人之間親密的體驗中,看到之所以必須「現身」與「缺席」的意義。這裡不是控訴父權文化的女性「不在場」,而是透過負片、透過陰影、暗沈,提出女性共同體的存在感。
李錦繡這種滲透式、從根底擴散,將拍照時的美好紀念的記憶功能翻轉了。拍家族照片的儀式真面目被掀開了,也掀開了帶有更多跨越現在時空的過往家族悲喜的集體潛意識。不只是慣性偽裝出來的笑容,而是把家族追憶像偷偷去牽亡一般,從另一種異質視界返回陽間、返回現實。家族過往的災難與不幸,宛如陰影一般地現身了,像台灣藝術家吳天章《春宵夢》系列那些皮笑肉不笑的肖像畫一樣,觀者感到被威脅,被無以名狀恐懼威脅[18]。
李錦繡運用負片所製造的反差效果,把最幸福亮眼的翻過來。但翻過來的並非就是不幸,而是更難以理解的神祕深淵。「家族系列」像內視鏡滲透到最內裡,觀者所看到的是什麼呢?是血源、血脈相傳,是血,是被避而不談的生理有機體的血的結合、血的孕育、血的慾望。這是構成生命可以活下去,延續血緣共同體的根基。而這個經血的根基,被以父權為主的慣俗貶抑母體體液分泌物的價值,視為不潔、污穢,所有人必須迴避的禁忌。這裡紅黑團塊的象徵,也具有對於傳統支配家族的父系權力秩序的圖像滲透感,以及在滲透感下的反思。
1.3 李錦繡的《通靈》
上述「家族系列」的人物畫,這些輪廓模糊的人物像,本來灰暗、留白的調性,卻被血黑團塊遮住、干擾。顯眼的血黑團是血的慾望,也象徵血緣的連結,原本已經互相面目模糊的家族成員,卻又被紅黑團塊給團團包圍。在靈性探討的角度上,我們或許可以關連到現在依然常見的華人社會民間祖源作祟的信仰。這些陰影般的血黑團塊,圈住了原先模糊與留白的疏離或是褪色的形象,就與靈魂的時空感上,也出現了不同的多重時空感的想像,讓「此生」、「前世」、「來生」界線互相滲透,陰界與陽界互相穿透。
李錦繡在1980年代初提出:「我主要的創作心思,在於全是由人所佔據的空間之神秘」。「人生不僅包括今世,也包括前世與來世,而今世、前世與來世,只不過是到達『最終目標』的暫時形式。」[19]「家族系列」的留白與血黑團塊併置的構圖,一方面具有回溯過往記憶的心理過程。另一方面,還同時帶有「抽離」原先的記憶脈絡,產生意義蛻變後的「投入—抽離」的兩面性。例如在《家族二》(1981)[20]「抽離」在此是指將觀者從原先家族照片的「團圓」、「凝聚感」拉出來,再拉向另一種不確定與疏離感。

這些隱晦的色塊在年輕的李錦繡1976年那幅《通靈》人物畫就已經出現了。那種以透視法的技法,運用不規則流動的抽象色塊,製造出錯亂、彷彿出神迷離、虛實難辨的變身幻境感。值得玩味的是,《通靈》版畫上的光腳丫子,也是那年李錦繡的同學林柏梁拍照中,她留下的腳丫子[21],在她的後期作品中也若隱若現。這張《通靈》版畫作於結婚之前,她那時期專注於變形,不管使用水墨、油彩或是水彩,顏色都是偏灰暗的色調,非常曖昧、混濁。畫面中人與人、人與空間的關係呈現出疏離與寂寞的存在感, 加上刻意被抹去的五官,有時彷彿像是一個個沒有身分的幽靈[22]。但這張《通靈》最令人驚奇的,正是她留白與淺色的運用。李錦繡說:「透明的空間,我的存在應也是透明自在[23]」。
畫面上通靈者看不出面容、性別,前方有張椅子,但通靈者彷彿騰空漂浮旋轉,通靈者身體的底盤卻中空,穿透背後牆面的透視線。通靈者這具身體的底盤不見了,變成留白。如果這位通靈者是生理女性,那她的底盤、作為生理女性最重要的性器官被透明化了。這也讓人猜測,孕育生命的陰部下盤與女性生理的經血的意象,是否李錦繡到了「家族系列」有了新現形。冷灰色系的這張《通靈》畫面,帶有一種曖昧的孤獨,雖然身體彷彿騰空,卻不像那些神佛仙班的自在,像是進入憂鬱的跨時空想像渦漩,或是正在進行累世因果的搜尋。這孤單的通靈者,獨自進入異世界,和「家族系列」的多人形影留白、看不清面容類似,卻都散發著人與靈性交流的空間想像。
「祖源」是現代台灣宗教人在傳統家族共同體衰微之後,依然透過形而上、「靈」的共同體、集體文化象徵,繼續影響進入小家庭、個人主義導向的台灣社會。在榮格心理學中「集體」是跨越家庭、族群、性別、世代、階級、個別文化之外的想像共同體,屬於無意識或靈性的整體感。而海寧格(Bert Hellinger)的「家族排列」理論裡,則看到「家庭」作為「靈魂」的共同體,有共同的動力,將曾經因為生物性的交配繁衍,所產生血緣和姻親關係,都視為家族共同體的靈魂成員。不管先後生死,都具有命運共同體的歸屬權,彼此的「靈」在生前死後繼續有所關連。記憶不只是活著的人這一輩子的記憶,還包含過往的家族成員,也被視為靈魂共同體的家族同心圓的一環[24]。
李錦繡在「家族系列」這些留白與淺色渲染的人形合照,他們也像是音容宛在的祖先,宛如祖先畫像的潛意識[25],更像是殘存在過世者印象中模糊的親情相聚。這些聚在一起的家族,像不同時間的生命體之間互相滲透。這是陰性「混沌」的滲透性,不是穿透,而是互相進入,生者與另一時空下的生命體互相因為因緣而聚合[26]。這些聚合在一起的人形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這種和過往的靈魂互相滲透的空間視覺感,也彷彿台灣們民間新興靈性運動中透過「開文」時,和過往的祖原、祖靈溝通一般[27]。
李錦繡「家族系列」的負片家族合照的寫實抽象化,並非復古懷舊,而是音容宛在的壓迫感。正如我之前所探討的吳天章人物像,透過肖像攝影寫實的表現形式,將欲望的動力與民間信仰的「靈魂不滅」或「魂魄」相結合[28],李錦繡也異曲同工。李錦繡的「家族系列」也引出自我意識無限延伸的想像,讓可見的「陽世」欲望延續到不可見的「陰間」,延伸到無止盡的生生世世輪迴的想像,彷彿愛憎癡狂的鬼魂不斷地透過「遺照」而「陰魂不散」。透過「形而上」的心理想像與「形而下」肖像攝影寫實表現的雙管齊下,時間差所形成的「舊」時代「老靈魂」魅影崇崇。
1.4「安寧注視」系列
李錦繡的畫面也以「凝縮」的「定格」,展現了作品內在時空意識在形象、結構與色彩上的變化關係。當觀者凝視畫面時,符碼意義的產生,就不只是將作者展現於內在畫面裡的靈感召喚出來而已,同時也透過作品在觀者的腦海中創造了嶄新的意象。這新意象透過畫面可見的材質形象,彰顯了內在畫面裡看不見的、隱匿在記憶與想像深處的歡樂與痛苦,以及難以言喻的畫境之外的奧秘[29]。
李錦繡在2003年因病英年早逝,在她面對死亡威脅壓力最後階段的時光,幾幅已完成的家人頭像畫「安寧注視」系列[30],卻完全跳脫年輕時期西方超現實技術的黯沉、看不清面容的疏離視角。這四幅「安寧注視」系列以近距離的正面家族頭像畫,如此逼近的凝視,折射出親人之間注視時的關注感、病重難以痊癒的壓迫感、來日不多的急迫感。李錦繡返回人性根源的凝視,跨越了個人的形體,是另一種形可形、非常形,充滿了曖昧又返璞歸真的聖像畫奧秘。這些圖像跳脫透視法的頭像,展現出一種巨大又模糊的「人」的存在感[31]。這些「安寧注視」系列乍看之下可以辨識親人隱約輪廓,再凝視,逐漸看不出哪一國人、哪一種年紀、甚至是不是專業藝術家所畫。尤其是對丈夫的凝視,看不出人像畫是喜是悲、是呼喊、是眷戀、是告別。
和看到「家族系列」的反應相反,我第一次從畫冊上看到「安寧注視」系列,一開始以為李錦繡因病而體力弱,難以掌握過去精湛畫風,畫出來的圖像宛若未受過藝術訓練的素人或孩童畫。但是仔細再看,我的看法改變了,我看到藝術家生命即將逝去時,將僅有的生命餘暉動能,跳脫透視法,採取最簡單的構圖、筆觸和色彩,以正面大頭照般的頭像畫,來凝視所愛的、所牽掛的家人。「安寧注視」的親人頭像面容,拋去了李錦繡卓越精準的寫實功力,返回到素人、孩童一般、率真線條的遊戲揮灑,跳脫了階級、年齡,罕見的曖昧暖色。
藝術家留給後世一種時代圖像,從個人對於自我生命、家族、朋友的關聯,是日常的關係、日常的倫理,但也跨越了藝術家的今世,進入另一種潛意識、生命內在、靈性的形上宇宙的靈魂與靈魂之間的透視[32]。這對已經習慣於3C科技產品與網路關係的現代人,李錦繡的這兩系列,依然像透視鏡般,提出個人面對家族在疏離、疏遠的留白模糊意象中,血色黑團塊的血緣DNA般的生命體的牽扯,依然音容宛在。
李錦繡:「多采多姿的現代繪畫於我言是遺產、是啟示。通過一個絕對真實的個人『我』,所謂的『自由』便是對所有藝術表現方式無執的觀視與超越。而超越的方式,是在不斷的忠實於自己『心安』的思考中。」[33]女性藝術家從個人與家族關係透視,到對於家族的過往靈魂、更擴大到集體苦難的面對與祝福,這也是另一位藝術家柳依蘭和李錦繡,作為妻子和母親,所面臨的女性生命圖像創作上相呼應的特色。
2. 柳依蘭的人物畫2013-2021

如果上面我以李錦繡的「家族」與「安寧注視」兩系列為焦點,探討受學院專業訓練、又跳脫學院的女性藝術家,如何看待家族與「自我」之間從有距離的透視,到逼近的凝視,從被迫隱藏、成為邊緣的透視者,到面對死亡大限、英年早逝前夕、對家族面對面的不捨、道別與祝福。接下來我要探討的另一位藝術家柳依蘭,我將集中在她2013年之後的幾幅畫作,探討這些藝術作品如何從家族的人性衝突,轉向到對於全球COVID-19疫情所產生的災難考驗,藝術家對於人物畫所透顯的跨越家族,進入人類共同體的意義表現。
柳依蘭作為從一位傳統市場勞動者,自學成為專業藝術家的女性菁英,在李錦繡作品中模糊的「自我」面容,在柳依蘭的創作中,則以誇大雙眸、緊閉厚唇的「我」無所不在,成為畫布中的唯一主角。這個「我」的面容在2008年過後,逐漸跳脫柳依蘭本人的寫實樣貌,以彷彿面具般,成為每位畫面角色固定的臉,有著藝術家對於生理女性或靈性「女性」的潛意識原型與畫面多重自我的角色扮演。
我印象中的柳依蘭,穿著名牌古典漢服現代風,近期裝扮也彷彿她畫中人物般的穿著,貌似冷漠孤傲的神情,透過創作追問著生命價值。李錦繡的「家族系列」的留白,是二十多年後柳依蘭用力地描繪的家族共同體人性鬥爭。1998年柳依蘭第一次拿起畫筆,2002年第一次開始在家裡作畫[34],林殷齊認為畫面上不斷重複出現的誇大眼睛有堅定、桀傲不馴[35]。柳依蘭把臉畫得很大,飽滿、巨大佔滿畫布上,讓觀者不得不正視,那是藝術家想要展示的「存在感」[36]。
柳依蘭的創作透過圖像,表現出經歷人性鬥爭的痛苦僵化、矯飾與扭曲,曾經宛如一位割肉餵虎的自虐藝術家。但柳依蘭逐漸地從這些僵化的、面具般的家族女性原型,加入了對於社會共同體的觀察、批判、憐憫、鼓勵與撫慰。二十多年來,柳依蘭的創作宛如一場接一場自我啟蒙的女英雄故事,讓記憶與想像從虛構幻見中,找到能量出口。柳依蘭打造出穿梭在家族、社會、靈性團體中,音容宛在的身分扮演[37]。 人物畫從負面的缺憾、質疑、控訴,轉為正面的安頓、成全與祝福,這是一種庶民的人生圖像劇場,觀畫者不是去看表演,也不只是去當演員,而是在畫作、藝術家與觀者之間,探索生命存在的意義。
2.1「面具」
「面具」(persona)是指為了外在社會環境而改變自己,彷彿戴了不同的面具,扮演不同角色,保護自我也遮蔽了自我。面具也代表一種人格特質或偽裝的人格特質[38]。柳依蘭畫布上的人物男女老少,為何總是帶著誇大雙眸、緊閉厚唇,無法卸下來的面具呢?這種面具形象讓柳依蘭即使畫孩子的形象,也宛如潛藏老人面容的詭異[39]。這是否反映了現今的女性,在這個社會表面平等,卻常以平等之名,承擔許多責任與包袱的現況。女性菁英透過自身的奮鬥,在階級上取得較為對等的身分,但這樣的比例依然是台灣社會的少數。
人們往往有兩種自我—外表的我,表現給別人看。內在的我或是真正的自我,面具讓外在扮演的自我與內在的自我得以矛盾共存。柳依蘭發現,大部分的人活在「別人怎麼看我」,而很少活在「我如何看我」,柳依蘭看自己的創作是「我如何看我」[40]。自畫像成為一種藝術家視覺符碼運用的自我內在探索,也帶有家族、地方、集體文化投射、人與物種的意義多元性[41]。
柳依蘭的人物畫構圖,雖然和李錦繡都吸取家族照片的視覺符碼,但是柳依蘭不是留白模糊,而是誇張扭曲。柳依蘭的人物所擺的姿勢,畫面出現典雅精緻的古董傢俱、盆栽植物、大型花瓶…等等,像是戲仿祖先肖像畫,也像早期到相館拍照的各種美好生活扮裝[42]。只是柳依蘭人物畫中最關鍵的人物的臉,卻翻轉了一般祖先肖像畫和美好時光老照片的意義。相館照相所常出現的美好、和諧、笑容,不管是否造假或炫耀,在柳依蘭的畫面上,人物畫招牌大眼和緊閉的雙唇,所產生怪誕視覺的反差,讓這些人物畫對照家族相片,將造假或炫耀的美好,變成對於粉飾太平的揭露與嘲諷。
柳依蘭畫中經常出現的艷色與強烈色彩對比,在紀錄片《南島盛艷之花》[43],她說一開始找不到自我,但她一直拼命找尋,彷彿強迫症般的焦慮。她曾說恨她媽媽、婆婆,在有意識的恨中,創作,誰的恨?這種畫作中所透露出的怨恨,不只是藝術家個人,而是藝術家的作品中吶喊出那些被壓迫、被拋棄者古往今來的集體恨意。這也是讓我感受到上述的李錦繡所認為的藝術,包含了生命不只是這一輩子,而是有共時性的前世與來生,和過往靈魂交會的機緣。一般肖像照重要的笑容很難找到。
2.2 女人
柳依蘭的畫裡面的故事是一代接一代女人跟女人的故事,像一千零一夜。這些女人是母親、婆婆、媳婦、女兒、情敵…等等的人性陰暗與光輝的折射。無法成為公主,但是卻變成婢女,在憤懣中忍辱、被迫扭曲自己,直到太后駕崩、直到苦媳熬成婆。這些故事像是「古老女人」原型的陰影,性格上是無情的、可怕的、憎恨的,或是期待的、自我犧牲的、祝福他者的… 。當觀者被這些畫面上怪誕面容的目光注視,也造成了壓力。因為觀者也可能在似曾相識的眼光底下長大,也想要擺脫這樣監視的眼光。看這些人物畫,有一種內在陰影被喚起。
柳依蘭人物畫刻意僵化的面具/面容,以及僵化造作的身體姿態,具有一種扮演的身體感。或許來自她對於過去出身階級的沒安全與自卑,但同時也凸顯了透過婚姻,女性成為以手工勞動力為主的家族媳婦,所面臨的父系社會對於已婚年輕女性的壓迫。柳依蘭和李錦繡一樣,在現實生活裡要扮演為人妻、為人母、女兒、媳婦,長期在勞力職場上,讓柳依蘭宛如李俊賢(1957-2019)所說的「孤女的願望」,藝術創作另一種變身、跳脫非自願性勞動的出口[44],不斷地穿梭在現實與自己想要創作的世界。
柳依蘭在《自我設限》(2011)[45],畫了一位綁兩條辮子、有點像懷舊電影的女性人物,一隻手和全身被包裏品般的紅彩帶綑綁了,上面寫著「知識」、「美感」、「品味」、「風格」的文字。另隻手拿一把菜刀,似乎要斬斷這些束縛,雙眸注視著遠方,像是童話故事中即將展開探險。這幅畫中的女性,可能是藝術家自己,似乎正面臨個人內在或創作上困境的突破。然而到了《熬成婆》(2013)[46]畫作中,這三位女性原型:少女、新娘與老婦,雖依然像過去的畫作,正經八百、端正的姿態宛若祖先畫像、或是古典人像畫,正視著觀者。不過,柳依蘭在這樣的構圖中,展現出對於生命、家族、婚姻的命運雙重時間感,一邊是線性時間感的階段蛻變對比,另一邊也是心理上共時性的女性原型,少女、新娘與老婦三位一體。


穿著古典華服的老婦,在柳的畫作中經常扮演權威、支配新娘/媳婦的角色,如同Erich Neumann所提出的負面大母神的人性陰暗面[47]。少女和新娘呢?她們又如何在家族共同體中,從單純、天真、無知、受照顧,進入被啟蒙、成長與蛻變,也包含人性中陰影的出現與面對。這張圖也流露出自我創傷的潛意識、防衛機制,自我在陰影中任性、自私、無情、殘酷,自我中心、自大、貪婪、暴力、脆弱、情緒化[48]。這三位女性的衣服都帶有漢服的文化圖案,誇張雙眸與緊閉雙唇同時在少女、新娘、老婦,究竟經歷了多少考驗與滄桑?在這個家族共同體的生命禮儀過程,她們依然正襟危坐,直視前方。
2.3 扮裝
柳依蘭所畫的人物不是李維菁小說筆下的二十一世紀初都市美少女戰士,為自己的情慾在血淋淋的人肉青春戰場上奮戰廝殺[49]。從柳依蘭的創作歷程和我對她的訪談中,我感受到她從對抗自身的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衝突奮戰,逐漸從宛如女戰士爭取平等與尊嚴的角色,轉向成為凝視他者生死、痛苦,承擔、療癒與撫慰靈魂的「巫」者。這種轉變讓她的創作有來自她所屬的「五年級」1960世代熟悉的「老派」時代性格,以及更古老的潛意識內在探索。
柳依蘭從2015年之後的人物畫,已經逐漸從家族人性衝突翻轉了,逐漸開始出現引起我關注的宛如薩滿、巫、或是宗教師的靈性角色扮演。柳依蘭近年來不再從事傳統市場的工作,曾經讓她痛苦的婆媳問題,可能也隨婆婆的去世而化解。女性菁英的身分,繼續透過創作,探索自我。過去她的人物畫,宛如一支支受傷、被咒詛的圖騰柱。她從自己家族角色所遭遇的怨氣,也宛如一面人性鬥爭的鏡面。她畫作中的臉,呼應著那些曾經以女性的古怪、醜陋、矯揉做作、緊張不安、惡靈、鬼魅一般的形象。只是鬼魅般的莊重、惡靈般的肅穆,這種莊嚴的扮演,反而展現出物極必反、反串的顛覆性,柳依蘭挑戰了以男性為主的性別權力結構下對於女性、對於家族的觀看慣性[50]。
中生代藝術家柳依蘭和新生代藝術家在創作上使用「扮裝」的手法不同,例如侯怡婷在「剝皮療」的變裝秀,以不同時代、地域文化符碼拼貼戲耍[51]。不同在於,柳依蘭很認真在扮裝,一點都不戲耍,一直認真扮演「苦旦」、「巫」和「神」一般的角色,嚴肅正經,和那些年輕世代女性冷眼旁觀或抽離、戲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有意識地透過身體扮演,顛覆男性凝視的策略不同。
柳依蘭的人物畫,從畫中人物穿著跨時代、跨族群的艷色服裝時,這些服裝被柳的畫風,轉換成柳氏的戲服,甚至畫面上宛如是品牌模特兒的服裝秀。柳依蘭並不混搭新世代藝術家帶有美日動漫扮裝的文化符碼,而是將這些她已經內化的對古董、漢服、懷舊日式花草服飾的品味,安置到她的圖像講古舞台。從2013到2021,不同系列的畫面上,從對家族身分與尊嚴的控訴,到關注如何追求「真我」、如何去面對社會動盪的全球COVID-19疫情的傷亡。她扮演一個她自以為的「自我」,卻透過這種認真而誇張地扮演,每一個「我」都是她自己,但也都不只是她自己。柳依蘭的圖像扮演有了儀式性的新意義。
扮裝是透過既有的文化符碼來模仿另一個角色,讓人對照、辨認,在辨識過程產生意義顛覆或翻轉的創意。性別越界的扮裝常被運用,女性藝術家的創作也被賦予性別議題的代言拉出更多光譜[52]。柳依蘭前期的創作,有意識地以孤女、怨女形象,畫出一系列女性角色的生命歷練,但這些有意識的文化符碼展現之外,讓我更感興趣的,是她創作中不斷重複的造型、色彩與技法。這種反覆如同儀式一般的圖像結構,反而像一種多寶格,可以掀開不同層次的潛意識或無意識的心靈內在,與更古老的心理原型的關聯。我可以看到從古老的祖先畫像原型,如何在新時代的柳氏多重自我的扮演,將古老的祖靈、祖源,不只是自己家族的老靈魂,而是屬於這塊土地上曾存在女性生命的縮影,注入藝術家個人運命的鎖鏈之中,例如《熬成婆》[53]、《她的名字叫婆婆》[54]、《不死的是愛情,不是愛人》[55]。
這和搭配電影《血觀音》[56]劇情的圓型構圖《遙遠的彼岸是彼岸花》(2017),那三位貌合神離的老、中、青女性對比一下,背後火紅的彼岸花,又有另一種呼應家庭親情支配與被支配的共同體張力,以及命運糾結的生死搏鬥輪迴般的奧秘。柳依蘭使用「圓形」構圖,她想表現有「圓形」的輪迴時空感。花是一種生命力,彼岸花卻是充滿旺盛死亡世界的邀請或示警。
2.4 階級
社會認同包含性別、族群、階級、世代…等等集體的文化影響,包含衝突、距離感與歸屬感。柳依蘭的人物畫在女性氣質的扮演,並非討好男性的手段,反而是產生距離感,看清楚這些女性氣質是後天的扮演,破壞父權體系的觀看慣性[57]。柳依蘭不斷透過將世人視為有品味、上層階級的物件、服飾,當成舞台與服裝道具。人物畫中的貌似上層階級,但是卻還保有她原先出身對不同階級差異的敏銳度,折射出這些被視為優雅、古典氣質的文化符碼所扮演的階級意識的功能[58]。李錦繡的「家族系列」人物畫,曖昧地展示現代社會共同體疏離的視覺化,傳統女性在結婚之後,變換身分認同的扭曲與壓抑。在柳依蘭的人物畫作品中,直接呈現對這種傳統漢人家族男女不對等的吶喊。

柳依蘭的《同心協力》畫作中[59],一再重複的招牌誇張雙眸,讓這些穿著典雅花色的少女們,乍看像一九六、七零年代精心打扮的富家小公主。柳依蘭不只描繪家族女性的人性鬥爭,也同時帶有對於社會階級的審視。不同於之前有明顯的華人衣著款式,這些少女們儘管黑髮,但已經難以辨識是亞洲人、還是其他黑髮人種。畫作中精心打扮的少女們,儘管衣著不同,但神情卻類似。精心打扮的少女們,腦袋裡裝的應該不同吧?還是被規格化了呢?這些戴口罩的少女,像反映現實的防疫,或是自以為潔淨、與周遭隔離呢?互相協助戴口罩,是同心協力、共度難關?還是互相監控提防呢?還是富少女的扮裝秀呢?這是一幅裝飾性強的畫作,人物重複出現的動作,只有那些有花草圖樣的復古式洋裝和同花色口罩,透露藝術家把衣著、口罩變成主角的巧思,少女們機械化動作變成宛如衣架一般。值得玩味~
柳依蘭不斷地創造一個又一個的「我」的角色,並不只是扮演「女性」,而是男女老少、神佛妖鬼、各式艷色花朵、還有「巫」。柳依蘭的畫布像是一幕幕說書人的命運劇場,扮演每一個角色都是「我」,但是帶著「我」的面具,每一個也都不是「我」[60]。從對自我的不滿與缺憾中,柳的畫作的扮演變成一種獨特的張力。自在或緊張、傷害或被傷害、慈悲或憤怒、精明能幹或遲鈍裝傻、堅毅或徬徨、嚴厲或裝可憐,都是扮演,像是引人看一齣齣身不由己的無言敘事。
2.5 靈性的兩面性—偽裝與祝聖
《時代的隨行者》(2018)[61]中,女性穿著是扮裝、是符碼,是性別化的社會建構。女性氣質的扮裝,反而產生一種不真實的距離感,彷彿提醒這只是扮裝,也折射出去思考這種扮裝的不同用意[62]。柳依蘭2018-2020的畫作中,這些「女性」氣質的扮演,依然不在於以外貌的魅力,去討好父權品味,反而是製造怪誕、詭異,彷彿帶著古老面具,讓觀者產生距離感。《真相之鑰》(2018)和《時代的隨行者》都以詭異的面容、最前方的領頭者手持蝴蝶型、斑斕鮮豔的權杖之鑰,《時代的隨行者》畫面上跟隨者是閉眼,《真相之鑰》的隨行者手持紫色花,和領頭者雙眸閉厚唇,表情一致。這樣遊行隊伍定格般的人物畫,像夢境一般,像扮裝秀、像遶境儀式一般,畫面上都是以女性形象出現。


不過,對照日常中以直男為主的生理「女性」形象 ,這些重複出現的柳式瞪大眼睛、似笑非笑的面容,這裡面所包含的「跨越」或「穿越」–這些「女性」扮裝難以辨識是哪種族群和年齡,彷彿返回古老的主持儀式者的莊嚴敬畏,或者故弄玄虛。畫面上暗色衣著的人物,看起來彷彿喪禮的隊伍,取名《真相之鑰》,耐人尋味[63]。這些面具般的側面,帶有古老原始部落圖騰般的五官,並非漢人的面孔,這樣的圖像彷彿古老人類的面具變種,遙遠而古老,對漢人而言,甚至帶有原住民部落的異族情調。族群的文化符碼也是扮裝嗎?
這種人物挺直身軀的姿態,到了《親吻大地》(二)(2021),又有了另一種肢體動作的形式,三位穿著及地長袍的「女子」,背後闃黑一片宛如大地、宛如暗夜。兩個人側身彎腰、向下插橙色菊花,還有一位手持口罩、躺臥的人,菊花彷彿也已經躺臥或種在深淵般暗色的畫面上。柳依蘭從菊花張牙舞爪、有秩序又有點脫序的花瓣,感受到菊花瓣在構圖上有助於線條張力的布局,又有「死亡」與「再生」的象徵。表現在她2022的菊花祭個展,她意識到大瘟疫時代的生命消逝,菊花宛如送別、不捨、紀念與追憶[64]。《親吻大地》(二)簡單的構圖元素,卻包含了藝術家對人類面對疫情暗夜的反思。一再出現的面容下的身體,這次彎下腰[65],甚至躺臥,身體像大地一般被踩踏。
.jpg?resize=1024%2C817&ssl=1)
結語
如果用榮格的心理類型的「抽象化」和「具體化」來看李錦繡和柳依蘭的人物像,的確是一種女性面對神聖共同體的兩種視覺化鏡面。李錦繡的「家族系列」從西式 抽象畫的特色,從整體選擇出部分,這一種選擇,就包含了對於「家族」共同體整體認知上的抉擇,將人物變成只剩輪廓線的留白,被消失的家族面容與唐突顯眼的血色與黑色團塊,產生了新的佈局上的神秘吸引力,怎樣的共同體的拼裝?是血緣、是彼此前世今生的陰影?這些抽象化的視覺佈局的抉擇,說明了音容宛在的共同體,難以言喻的傾訴,留白之處也有無以名狀的奧秘。像是咒詛一般、還是血緣奧秘一般的血色黑色團塊,抽象化過程中產生了重要與不重要的外在造型與價值的區分,正如「安寧注視」系列返璞歸真的抽象化,產生了另一種對於共同體最後凝視的深意。
相對於李錦繡,柳依蘭的具體化又意味著怎樣的造型抉擇呢?抽象化是封閉、獨立、切割,具體化是連結、不斷混搭、不斷將原先的感覺、想法打散、打亂,加入其他有關聯或沒關聯,或是失去原先的連續性。不管是被迫還是主動。網狀。矛盾、沒有一致性。情感越具體越主觀[66]。柳依蘭的人物畫彷彿帶著古老面具,從對自我的不滿與缺憾中,傷害或被傷害、慈悲或憤怒、精明能幹或遲鈍裝傻、堅毅或徬徨、嚴厲或裝可憐,都是扮演,也都是人生。
作為一位認真面對現實、追求自我的藝術家,李錦繡和柳依蘭的作品讓觀者思考,如何面對社會變遷中「神聖」的共同體。這是個人現況上的人性剖析與透視,也是靈性上所面臨的個人與今生的家族、甚至古老「家族系列」之間,命運共同體的潛意識,或是集體記憶的互相了解、解冤釋結、祝福共存。當我們說繪畫展現了內在時間的空間化,這種看似和外在物理時空不同的體驗,不正是包含了彷彿萬物有靈般的感通嗎?這些出現在畫面裡的形象、佈局與色彩,有用的、無用的、高雅的、低俗的,都曾讓創作者深深地著迷與受苦於難以呈現的折磨,卻又深深地享受著這些被召喚出來的視覺符碼,在結合與衝突過程中所帶來的一次次驚奇[67]。萬物進入創作者之內,創作者在萬物向她顯現時,她也一個一個地進入他們之中,不斷地透過畫面,讓觀者加入這些人物畫的意境,去探索人心與萬物之間內在生命的交融。
[1] 本文完成感謝黃步青老師、柳依蘭女士、林英玉先生的協助。
[2] 李錦繡簡介參見https://next-art.tainan.gov.tw/index.php?inter=star&category=4&year=2017&id=57。
李錦繡畫作請於台灣創價藝文學會製作的《游移空間的對鏡—李錦繡的生命藝術》短片中瀏覽:https://www.sokaculture.org.tw/exhibition/%E6%B8%B8%E7%A7%BB%E7%A9%BA%E9%96%93%E7%9A%84%E5%B0%8D%E9%8F%A1-%E6%9D%8E%E9%8C%A6%E7%B9%A1%E7%9A%84%E7%94%9F%E5%91%BD%E8%97%9D%E8%A1%93
紙本畫作請參閱:王素峰,《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特刊(台北:臺北市立美術館 ,2006)。
柳依蘭的經歷、作品與評論,詳見柳依蘭個人網站http://www.liuyilan.com/index.html,本文所附柳依蘭畫作圖檔,特別感謝柳依蘭女士的慷慨授權。
[3]如果宗教是指人與人最親密的連結,那家族就是華人社會到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宗教。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曾指出漢人「真正的宗教是拜自己的祖先」。詳見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 馬偕台灣回憶錄》(台北 : 前衛, 2007),頁121。
[4]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台北:前衛出版社,2016),頁07。
[5]杉浦康平,《造型的誕生》,李建華,楊晶譯(台北:雄獅美術),前言。
[6]杉浦康平,《造型的誕生》,頁170
[7] 關於神聖的顯現,我延伸了伊利亞德的理念,詳見王鏡玲,〈在百科全書式的旅途中漫步:一種閱讀Mircea Eliade的方式〉《聖與俗》後序,收錄於Mircea Eliade, 《聖與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楊素娥譯(台北:桂冠,2001)。頁291-293。
[8]艾莉森.沃爾夫(Alison Wolf),《女力時代:改寫全球社會面貌的女性新興階級》(大塊,2015),頁10。沃爾夫雖然分析的是歐美社會,但是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也同樣具有社會變遷的時代特性。
[9]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
[10]王鏡玲,〈「開文」與個人「神話劇」—台灣民間「通靈」現象探討〉,東海大學「靈異經驗與哲學反思」工作坊會議論文(2021.12.17)。
[11]詳見榮格(C.G. Jung),《榮格自傳》(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劉國彬、楊德友譯(台北:張老師文化,1997),第六章:正視潛意識。
[12]王鏡玲,〈非真之真,非假之假?–試窺吳天章的視覺意象〉,收錄在《慶典美學》(台北:博客思出版社,2011),頁081。台灣家族紀念照的歷史變遷,參見賴佩君,《台灣家族紀念照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39-44。我最近策展(2022)的彰化市福安里家鄉老照片展,也發現自1960年代後期開始日常生活的照片,逐漸出現在一般中產階級人家。
[13] 王素峰,《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台北:臺北市立美術館 ,2006),頁44。
[14]我在2008年在金枝藝術(苗栗苑裡)舉辦的「金枝莩蘡• 歡喜開幕」聯展,第一次現場看到李錦繡的作品。
[15]「歹物仔」台語拼音pháinn-mih-á,指鬼怪、超自然或不祥、不潔的人或物。
[16]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92-96。
[17]林殷齊,《女性藝術家自我實現的歷程 柳依蘭的畫與話》,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論文(2014),頁134。
[18]參見王鏡玲,〈非真之真,非假之假?–試窺吳天章的視覺意象〉,《慶典美學》,頁076-111。
[19]李錦繡,《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頁16。
[20]圖片來源,李錦繡,《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頁85。
[21]林柏梁攝,《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頁190。
[22]謝佩家,《黑色團塊下的情感交疊-李錦繡早期作品析論(1975-1982)》,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40。
[23]李錦繡,《李錦繡素描集》(台南:東門美術館,2005),頁4。
[24]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031。
[25]《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頁84,賴佩君,《台灣家族紀念照研究》,頁56。
[26]例如李錦繡,《家族四》、《家族五》,《竹凳的移動:李錦繡紀念展》,頁84-85。
[27]詳見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第四章能量的戰場──海邊「普化」儀式探討和第五章神話口述與通靈象徵──「天山老母」女乩現象。
[28]參見王鏡玲,〈非真之真,非假之假?–試窺吳天章的視覺意象〉,《慶典美學》頁79。
[29]王鏡玲,〈偷夜之夜,偷歡之歡—進入林英玉的畫境〉,https://artemperor.tw/focus/16。
[30]李錦繡的「安寧注視」系列畫作,請參考「藝術天堂」網站,陳韻琳撰寫的《李錦繡的『空竹凳』》:https://life.fhl.net/Art/art/art_09.htm。
[31] 關於聖像畫詳見聶書嵐(Solrunn Nes),《神祕的聖像畫:Icon的技法與意涵》,盧玫君譯(光啟文化,2011)。
[32]王素峰,《李錦繡〈任遨遊〉》(台南市文化局,2016),頁22-23。
[33]嘉義市文化局,《藝術路上.自在觀:李錦繡返鄉紀念畫集》,嘉義:嘉義市文化局,2006。頁16-17,引自謝佩家,《黑色團塊下的情感交疊-李錦繡早期作品析論(1975-1982)》,頁98。
[34]林殷齊,《女性藝術家自我實現的歷程:柳依蘭的畫與話》,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論文(2014),頁94-95。
[35]林殷齊,《女性藝術家自我實現的歷程:柳依蘭的畫與話》,頁106。
[36]根據2022.02.13我在新苑藝術柳依蘭個展現場對柳依蘭的訪談。
[37]關於柳依蘭的創作參見林殷齊,《女性藝術家自我實現的歷程: 柳依蘭的畫與話》, 有柳依蘭從小到2013年創作的歷程探討。
[38] Robert H. Hopcke,《導讀榮格》,蔣韜譯(台北:立緒,1997),頁86-87。
[39] 例如柳依蘭,《冷眼繁華》(2013)。
[40]林殷齊,《女性藝術家自我實現的歷程: 柳依蘭的畫與話》,頁33-34。
[41]同上書,頁54。
[42]賴佩君,《台灣家族紀念照研究》,頁52-53。
[43]盧彥中導演,紀錄片《南島盛艷之花》(2013)。
[44]李俊賢,《鏡花逐夢》(高雄:高苑科大藝文中心,2009),頁4。
[45]油畫,91.5 x 73 cm。
[46]油畫,230 x 100 cm。
[47] Erich Neumann,《大母神—原型分析》(The Great Mother :The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李以洪譯(北京:東方,1998),頁149-194。
[48]莫瑞.史坦(Murray Stein),《榮格心靈地圖》(Jung’s Map of The Soul)(台北:立緒,2017),頁138-139。
[49]李維菁,《我是許涼涼》(台北:印刻,2010)。
[50]吳曼榕,《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扮裝表現之認同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93。
[51] 同上書,頁99 和頁145。
[52] 參見陸蓉之,《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史》,(台北:藝術家,2002),頁16-17。
[53]《熬成婆》,油畫,230x100cm,2013
[54]《她的名字叫婆婆》,油畫,230x120cm,2013
[55]《不死的是愛情,不是愛人》油畫,230x130cm,2014。
[56]楊雅喆導演,《血觀音》(2017)。
[57]吳曼榕,《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扮裝表現之認同研究》,頁27。
[58] 例如參見柳依蘭《人與鏡》系列(2008)、《生命之曲》系列(2009)。
[59]《同心協力》,油畫,190x75cm,2020。
[60]林殷齊,《女性藝術家自我實現的歷程: 柳依蘭的畫與話》,頁120。
[61]《時代的隨行者》油畫,100 x 230cm,2018。
[62]吳曼榕,《台灣當代女性藝術家扮裝表現之認同研究》,頁18。
[63]《真相之鑰》,油畫,85X190cm,2018
[64]根據2022.01.14和2022.02.13對柳依蘭的訪談。
[65]根據2022.01.14和2022.02.13對柳依蘭的訪談。
[66]榮格(C. G. Jung),《心理類型》(下) ( Psychological Types ) 吳康、丁傳林、趙善華譯(台北:桂冠,1999),頁472。
[67]改寫自王鏡玲,〈偷夜之夜,偷歡之歡—進入林英玉的畫境〉,非池中藝術網 https://artemperor.tw/focus/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