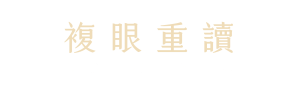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鄧元尉(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什麼時候當共在的「我們」以民族、國家或任何名義結成一個排斥性的共同體時,不在場的上帝就抵制並批判這個共同體。因著上帝,「我們」不能是任何一種同一性原理,也因此「我們」的內在有可能持存著「他們」。這個「持存他者的自我」或「持存他們的我們」,才是上帝與其子民之約所構成的共同體,一種不斷容讓上帝以其超卓的他異性挑戰、質疑並打破自我與我們、讓他者與他們得以獲得「生存空間」(Lebensraum)。
南國猶大被巴比倫滅亡時,先知耶利米從頭到尾目睹這個國家的傾覆,他曾疾聲呼籲君王與百姓遵守上帝與以色列人立的約,卻遭到漠視。耶利米代表上主如此宣告: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那使太陽白日發光,使星月有定例,黑夜發亮,又攪動大海,使海中波浪匉訇的,萬軍之耶和華是他的名。(耶利米書31.31-35)
這段經文後來在新約中得到呼應。希伯來書的作者主張,耶穌帶來了「更美之約」,因為「前約」有所瑕疵,基督徒則尋求「後約」。這位不知名的作者如此引用耶利米的宣告:
所以主指責他的百姓說: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不像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他們不恆心守我的約,我也不理他們。這是主說的。主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不用各人教導自己的鄉鄰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主;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寬恕他們的不義,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既說新約,就以前約為舊了;但那漸舊漸衰的,就必快歸無有了。(希伯來書8.8-13)
比新更新、比舊更舊的重重錯置
對基督徒來說,前約或舊約(摩西之約、律法之約)已經過去了,後約或新約(基督之約、恩典之約)取而代之。自從耶穌基督之後,人類就生活在新約時代。相較之下,仍然遵守摩西之約的猶太人,彷彿置身於已被廢棄的遙遠過去。於是,在新約時代的任何一個時間點上,憑藉著舊約來生活的猶太人都成為了「時間錯置」的例證,他們被視為緊抓著陳舊的律法、抗拒全新的許諾、固執地生活在毫無指望的歷史廢墟中。
在基督徒眼中,猶太人活脫脫就是時間錯置的典型,特別是在西方世界進入「現代」(modern)之後。「現代」即意味著永遠不會過時的「新」,新而又新,如此持續下去。在這個以「現代」自許的基督教世界中,沒有任何東西是太舊的,一切都處在不斷更新的過程中。當整個歐洲快速前進、邁入越來越新的時代,猶太人卻始終顯得格格不入,穿戴著不合時宜的服裝,僵化地遵守古老又古怪的律法,既蜷縮在城市骯髒擁擠的角落,也蜷縮在中世紀的時代灰燼中[1]。這一群人被世界所遺忘,他們也遺忘了世界。就像猶太化學家李維(Primo Levi)所說的,猶太人就像是氬氣(Argon),一種存量豐富的惰性氣體,為數甚多卻安於現狀,難以與其他事物產生化學反應。隨著基督教世界愈加急促地往前進發、邁向其凱旋的終末之日,猶太人卻凝固在時間的沉積中,二者的對比也愈加鮮明地呈現出時間錯置的特徵。
然而,猶太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對耶利米的話給出與希伯來書的作者截然不同的著重點:新的約是被寫在心上、放在心裡的,而且是不可教的,彷彿所有人都已然知道這個約。這是一個不可被告知的約,無論是透過他人、透過經典、或透過傳統而得知。我們無法從自身之外去得知這個約,我們只能在自己心裡去發現它。因此,這個另立的新約彷彿具有康德先驗道德法則的性質,但它又不是先驗的道德法則,因為它是被上帝(一位絕對的他者)寫在我們心版上的,而非源於道德主體之善意志的自我立法。上帝像是在夜裡偷偷的把這個約放在我們心裡而不為吾人所知,在我們發現它之前,不知道它早已存在了多久。簡言之,這個新的約,彷彿是先驗的,卻又是後天的;彷彿是主動的,卻又是被動的;彷彿是自律的,卻又是他律的;彷彿是全新的,卻又是陳舊的。
這重重的錯置關係意味了:相較於猶太人必須努力學習去實踐的摩西之約,這個「新立的約」並沒有在線性時間的意義上、或是時代的意義上比較新。列維納斯刻畫它的方式是:「比新更新、比舊更舊」。這是一個早就銘刻在吾人心版上的約,我們早就默默遵從了它。它比摩西之約更早,但唯有在摩西之約遭到挫折與質疑後我們才能領會它。這個新的約既是摩西之約的基礎、又是其實質,但唯當摩西之約因其不合時宜而在時間錯置造成的裂隙般的存在方式中,我們才得見此一既更舊又更新的約。相較於此,如果我們以線性時間的方式來理解這兩個約的關係,便很容易把它們共時化,如基督教把二者編在同一部經典裡那般。但即使如此,這兩個約的錯置關連始終在發生作用,這是基督徒也一直隱約意識到的,從而不斷在舊約中尋找帶來新約的基督的身影。基督徒選擇性地遵守某些摩西律法或強調其歷久彌新的信仰意義、並選擇性地將某些摩西律法視為陳舊過時的時代因素,或許可視為在線性史觀中實踐兩約之時間錯置關連的策略。
以時間錯置來領會「上帝與我們」的關係
這個另立的新約,把時間錯置的概念帶入人與上帝的關係。不過,我們還需要思考得更多,因為無論是摩西之約還是新的約,都不是給予個人的,而是給予「子民」,給予一整個民族,換言之,是給予「我們」。這意味了,我們需要藉由時間錯置來領會的關係是「上帝與我們」,更確切說是一種三重關係:上帝、我、以及我的鄰舍。
在列維納斯看來,我的鄰舍是我的他者,上帝則是他人的他者,也就是外於他者的他者。這位「外於他者之他者」具有比他者更超卓的他異性,是吾人絕然無法掌握的,從而也保證了他人之他異性亦始終超出吾人之掌握。在「我們」中,他人與自我共同在場,但他人何以持存為他者?關鍵不在於他之相異於我,而在於使他與我之所以能夠結成「我們」的上帝。自我與他人之在場而成為「我們」,關於這個「我們」,如果進一步成為某種同一性原理、產生某種共時化的整體,就有可能帶來排斥:「我們vs.他們」。「外於他者」之上帝則意味了上帝的不在場,不在場的上帝以其之不在來抵制一切在場的真理,後者作為共時性的成就亦是我思之成就,是以「我們」的共同體來標誌的成就。不在場的上帝則無法被我思共時化,以致於祂在思想中只呈現為一道「經過的痕跡」。這痕跡是上帝經過「我們」這群人所留下的見證,這個見證如今以他人的他異性表現出來,也以「我們」的內在裂縫的形式表達出來。什麼時候當共在的「我們」以民族、國家或任何名義結成一個排斥性的共同體時,不在場的上帝就抵制並批判這個共同體。因著上帝,「我們」不能是任何一種同一性原理,也因此「我們」的內在有可能持存著「他們」。這個「持存他者的自我」或「持存他們的我們」,才是上帝與其子民之約所構成的共同體,一種不斷容讓上帝以其超卓的他異性挑戰、質疑並打破自我與我們、讓他者與他們得以獲得「生存空間」(Lebensraum)[2]。
摩西之約表面上是一套律法,實際上它創造了以色列人,創造了猶太人,一群活在時間錯置中的上帝子民,同時也是一群始終無法被界定的「我們」[3]。耶利米預告的新約再次強調了「子民」這個身分:「我要做他們的上帝,他們要做我們的子民」。「上帝—子民」的關係必定是時間錯置的關係,這層關係被寫在心版上,無法被教導與被告知。這層關係早已存在於自我心裡、存在於我們當中,在這意義上,它總是「舊」的。然而,這層關係只能透過對某種已知曉的關係的突破而來,在這意義上,它總是「新」的。曾經,摩西之約是表達這層關係的其中一種被表述出來的形式;如果基督教要繼承這個約、繼承這份關係,那麼,理當是讓「教會」也成為表述此一「上帝—子民」關係的形式,一種未曾有過的、但如今透過耶穌而得以可能的形式。這正是使徒保羅曾經表達過的,他曾這麼說道:
我們豈是又舉薦自己嗎?豈像別人用人的薦信給你們或用你們的薦信給人嗎?你們就是我們的薦信,寫在我們的心裡,被眾人所知道所念誦的。你們明顯是基督的信,藉著我們修成的。不是用墨寫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心版上。(哥林多後書3.1-3)
保羅的讀者、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就是被聖靈寫在保羅心版上的「他們」。上帝把新的約寫在猶太人心裡,也寫在基督徒心裡。猶太教與基督教之間的關係(如果二者間可以建立起關係的話)並不是孰新孰舊,而是在新舊的時間錯置中開展出的群體錯置關係,而這涉及某種在時間錯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共同體,一種無法被整體化的共同體,一種無法共時化的共同體,一種在邊界上相互鑲嵌的共同體。這是一種始終以差異為導向的共同體,借用南希(Jean-Luc Nancy)的用語:此一共同體乃是沒有共同存有(common being)的「存有於共中」(being-in-common)。
[1] 猶太人的中世紀一直延伸到啟蒙時期才漸趨告終。
[2] “Lebensraum”這個德文字是納粹德國用以擴張領土的用語,列維納斯則反過來要求在自我當中為他者騰出生存空間。
[3] 雖然基督徒很想界定清楚「猶太人」,因為沒有「舊」約就沒有「新」約,沒有被清楚界定的猶太教、就沒有被清楚界定的基督教。
參考文獻
Levinas, Emmanuel, Difficult Freedom: Essays on Judaism, trans. Seán Hand, Baltimore: The John Hopl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Levinas, Emmanuel,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trans.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1.
Levinas, Emmanuel, “God and Philosophy,” in Basic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Adriaan T. Peperzak, et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Nancy, Jean-Luc, “On Being-in-Common,” in Community at Loose, ed. the Miami Theory Collectiv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