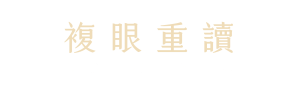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黃奕偉(政治大學宗教所博士)
早春,福岡的清晨陽光燦爛。搭上空港線地鐵,從機場只需十分鐘就能抵達鬧區博多,這個聽到名字就會聞到豚骨拉麵氣味的地方,四通八達的鐵道通往九州各地,大批推著行李廂、揹著背包的旅客會在此下車,我的目的地則是下一站,祇園。祇園是博多的舊街區,神社與寺院林立,為了方便遊客走訪,每個地標還都貼心地展示出歷史之旅的路線圖,好似深怕旅人錯過了這些在街頭比肩的深山名剎。
走出祇園站,對街即是東長寺,抬起頭就可以見到探出樹梢、金光閃閃的五重塔塔尖。東長寺是空海大師於大唐修業完成,返回日本創建的第一座佛寺,東長這一寺名有著祈願密教能長久流傳於東方的寓意。寺內二樓供奉著福岡大佛,高10.8公尺,是日本最大的木製坐像。更特別的是,在佛像的基座設計了一條讓信眾可以走入體驗的「地獄、極樂巡遊」。沿著黝暗的通道入內,牆上依序展示著從三途川、閻羅王審判、賽之河原、無間地獄、大焦熱地獄、大叫喚地獄、餓鬼道、畜生道、阿修羅道的一系列地獄圖像。走到阿修羅道後,眼前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獨自入內的我以為已到盡頭,只能循原路返回起點,在入口處確認還有極樂世界之後,我才硬著頭皮從三途川再走一遍,摸著牆在黑暗中蜿蜒前行,轉了不知道幾個彎之後眼前才依稀放光,暈黃燈光處是多尊菩薩照像,更往前一些則是西方三聖圖。我進入不久,另有一群遊客也步上地獄旅程,他們人多膽壯、在黑暗中小聲驚呼、打打鬧鬧,很快就趕上我來到佛像前。在大佛腳下,注視著圖像中被穿刺、在熊熊烈火中燒灼、在油鍋中烹煮的扭曲肢體,由黝暗至光明的地獄與極樂世界,對當代人來說,除了當作某種獵奇的旅遊景點,這些宗教圖像還有意義嗎?換個宗教心理學的問法,地獄的圖像與信仰是否、如何、又對人們發揮什麼作用呢?
地獄信仰的演化心理學解釋
關於地獄的信仰是有功能的嗎?從演化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信仰一個重視道德、會懲罰人的神可以促成社會合作,也為文明的進展奠定基礎。特別當農業進步,人類開始定居,人口數也隨之增加,逐漸組成更大型的社會團體時,大團體成員彼此陌生的匿名性削弱了原來以家族血親為根底的合作基礎,也帶來欺騙和搭便車等有益個人生存,但卻不利於群體適應與演化的行為(Launonen, 2022:195)。
如何解決大團體中,你我非親非故,卻可以自我犧牲而追求利他合作的問題?演化心理學家以「大神理論」(Big God theory)來說明宗教如何促進大群體的合作(Launonen, 2022:196)。大神理論有幾個論點與我們目前的問題相關,首先是「眼球效應」,這指的是人在被監看的狀況下,總是會表現得更有道德,並且這樣的注視,並不必然需要有形的眼睛,舉凡是請勿亂丟垃圾海報上的眼睛圖像(Launonen, 2022:196),或者像是民間故事中在每年農曆12月24日都要回到天庭稟報家庭是非功過的灶神,都反映著這種藉著被監看、甚至僅是單純想到有個在天上監管道德行為的神與利社會道德行為的關連。
於是,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推論,當群體越來越大,從部落、城邦到國家,所需要的監督就越強,換句話說,那位監管道德的神就需要更大、更有力量,因此也可以看到,從亞伯拉罕體系的一神宗教,或者抱持業報信仰的印度教與佛教,宗教往往與道德密不可分(Launonen, 2022:197)。再更精確一點說,這種道德意味濃厚的大神理論,就演化心理學的觀點,往往更重視地獄甚於天堂,理由無他,地獄中的永恆烈火,對比天堂中的樂音繚繞,更能掃除前述搭便車與欺騙等不利社會的行為(Launonen, 2022:196)。
有趣的是,這樣的推論,也就是地獄比天堂更有效、更能解決反社會行為的想法,在現代人心中似乎依舊成立。Azim Shariff和Ara Norenzayan這兩位心理學家就認為:
如果諸神使人良善,那可能是因為祂們的懲罰傾向有可信的威脅。因此,超自然懲罰假說(the supernatural punishment hypothesis, SPH)預測,對超自然力量的恐懼和懲罰的信仰應該與誠實行為相關,而與神的善良、慈愛方面的信仰則相關性不高(Shariff and Norenzayan, 2011:86)。
他們設計了一個作弊實驗,要求61位參與者進行二十題簡單的數學加法測驗,然後刻意製造實驗的失誤,也就是讓測驗的答案會自動在題目出現的幾秒鐘內顯現出螢幕上,並且要求受試者要在題目呈現後立即按鍵作答,如果是看到答案才作答,則被判定為作弊。實驗完成後,受試者並且填答了內在宗教性的量表以及神觀問卷等等,以分析作答情形與神觀、宗教性的相關程度。研究結果與超自然懲罰假說的預測一致,宗教投入程度、有沒有宗教信仰都與作弊行為沒有相關性,但是個人在負向神觀(像是:懲罰的、報復心強的、憤怒的、忌妒的、令人恐懼的…等等)的分數越高,作弊程度越低。
Azim Shariff和Mijke Rhemtulla(2012)更進一步對比了地獄及天堂信仰跟國家犯罪率的關係,他們從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s)與歐洲價值調查(European Value Surveys)等資料庫中蒐集關於地獄與天堂信仰、宗教參與程度等資料,以之對比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所統計,包含兇殺、搶劫、強姦、綁架、攻擊、竊盜、毒品犯罪、汽車竊盜、入室竊盜和人口販運等十項重罪的各國犯罪率,統計結果也同樣顯示相信地獄的人口比例與犯罪率有負相關;反之,相信天堂的人口比例則與犯罪率有正相關。如果與GDP或收入不平等其他變項相比,地獄或天堂信仰對國家犯罪率有更高的統計預測效力。他們認為這個跨國趨勢的比較,可以看出關於懲罰與全知的超自然力量信仰之所以會在歷史上與各種社會中廣泛傳播,主要就是因為這樣的信仰可以促進匿名陌生人之間的相互合作,並且能夠抑制不利社會的行為(Shariff and Rhemtulla, 2012:3)。
到這裡,我們已經某種程度可以回答地獄信仰的功能問題。借助演化心理學對群體適應與利他行為的理論關注,就既有的實證研究結果來看,無論是國家層級或者個人層面,地獄信仰看起來都與較低的犯罪率、較少的作弊行為相關,就這樣的實驗結果做推論,似乎可以與前述的超自然懲罰假說相互印證,因而做出大神理論、地獄比天堂強等推論,地獄與超自然懲罰的信仰在這當中確實發揮了促成社會合作與群體適應的功能。那地獄圖呢?當我們在地獄極樂巡遊中,無論是感覺到揣揣不安、抑或是在其中嘻笑打鬧,地獄圖像作媒介物,又發揮了何種作用?
地獄圖像作為宗教媒介物
針對宗教與圖像的關係,從宗教傳播的角度,宗教總是試圖從已知來傳達未知,藉由內在性來表述超越。媒介物做為所採用的具體手段,就擔負起在內在性與超越性之間進行調解的功能,也因此,像是地獄圖這樣的媒介物,就以其特殊的知識論位置引人注目。藉著討論這樣的圖像,就能夠相當程度帶領我們思索圖像對某人意味著什麼?又如何來意指這些東西?(Jurczyk, Krech, Radermacher, & Stünkel, 2023)
Jurczyk等人(2023)所指認出的宗教媒介物以內在表述超越的想法,轉譯成心理學語言,就與人如何對外在世界產生內在表徵有關,也因此當我們想要理解地獄圖象的意義,甚至追問人如何感知進而理解這些地獄圖象,關於視知覺心理學的討論就無可避免。2000年獲得諾貝爾生醫獎的神經科學學者肯德爾(Eric Kandel)在《啟示的年代》一書中,就通過對視覺感知的分析來討論維也納1900,克林姆、柯卡西卡與席勒三位藝術家的表現主義作品,借用他的思路,或許我們可以略窺宗教圖像可能帶來的心理意涵。
地獄圖像的認知心理學分析
針對藝術觀看行為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個層次:首先是觀看者對於藝術作品的外顯行為反應,其二是借助認知心理學分析觀看者的作品知覺、情緒與同理反應,最後則是試圖為觀看者的反應找出腦部運作機制(黃榮村譯,2021:226)。肯德爾認為在外顯行為與腦部生物機制之間,針對中間歷程,也就是知覺與情緒如何表徵的認知心理學分析,是連結藝術與科學的關鍵。
視覺資訊進到網膜之後,傳到視丘的側膝核,接著抵達大腦枕葉的視覺皮質區,之後分別傳送到大腦各部的三十多個區域,在這當中,兩條平行的主要通道,分別是傳到顳顬葉處理色彩、複雜形狀、身體、臉部辨識的內容通道(what pathway),以及傳到頂葉,處理位置空間訊息的位置通道(where pathway)(黃榮村譯,2021:249-250、291頁)。在這些已知的生物歷程以外,關於中間的認知心理歷程,肯德爾則是通過線條與形狀、色彩、深度、運動以及特化的臉部辨識來分別進行討論。
稍微加快一下分析的進度,通過這些個別視覺元素,圖象如何引發觀看者的情緒?以席勒在1915年所畫下的〈戴條紋臂章的自畫像〉為例,[1]這位在畫作中強迫性自我揭露的畫家,常通過扭曲而誇張的身體,刻意孤立凸顯的主題圖像,兩眼眼距過大且失焦、橘色頭髮等突出的臉部特徵,加強一種不安定的焦慮感,席勒將自己畫得像個小丑或是搞笑藝人,那似乎體現了一種在每天生活之中不斷被外界與內在刺激夾擊,難以適應社會的深沉內在恐懼。席勒特別善用「會說話的手」來凸顯主題,戲劇性向外伸展的手指像是被砍下的樹枝,或是歇斯底里患者異常扭曲運動障礙的手指,這些線索都似乎隱喻著對瘋狂的驚恐,以及預期(黃榮村譯,2021:191-198)。
席勒的作品顯然會激發觀賞者強烈的情緒,為什麼?最直接的原因是突出且不尋常的臉部表情。與辨識其他物體相比,人腦有更多的區域特別用來作臉部辨識,目前已經可以定位出在下顳顬葉有六個區塊專門做臉部辨識,這六個腦區也同時連結到前額葉皮質部(與美感、道德判斷、決策有關)與杏仁核(與情緒有關)。肯德爾認為大腦以臉部為優先處理的訊息,對臉部的辨識也連帶激發關於情緒與感覺的訊息(黃榮村譯,2021:334)。
就如同大腦特別注意到臉部,人腦對手部、特別是運動中的整個身體也透過不同的腦區來處理。席勒扭曲與誇張的人像肢體,似乎是要透過身體來盡其所能誇張表現出內在情感,而這些誇張的圖像加上前述的臉部訊息,更會誘引觀看者在無意識中模仿圖像中的姿勢與表情,此時,如肯德爾所言,觀看者的身體已然成為席勒情緒的演出舞台。席勒藉著扭曲自己的身體來揭露自身的內在衝突,同時也讓這樣的圖像成為中介,引出了觀看者的同理反應(黃榮村譯,2021:341-342)。[2]
此外,表現主義藝術家也善用誇張的顏色來引發情緒,席勒就特別偏好蒼白陰森的色調,〈戴條紋臂章的自畫像〉中最鮮明的顏色出現在被刻意突出的臉部和手指上,橘色和紅色在這樣的對比中絲毫沒有帶來暖色調應有的情感溫度,反而是在對比下更顯不詳。一般而言,對情緒的評價與觀看者的背景脈絡有關,也因此顏色引發的感受本就是曖昧的,對不同觀看者可能引發不同的情緒反應,但可以確定的是,人腦在辨識顏色上,比知覺到物體的形狀與運動快了一百毫秒,這樣的時間差就像是我們還沒認出這是誰的臉,就已經可以感知到臉部表情,也因此在認出是誰之前,情緒就已經先定調了,同樣的,色彩也會如此賦予線條與形象情緒意涵(黃榮村譯,2021:345)。
回過頭來看我在地獄極樂巡遊中所見的圖像。[3]肯德爾通過對臉部、身體與色彩的分析,來理解藝術如何引發情緒的想法,在各類地獄圖像中也同樣可以成立。地獄圖像中在閻羅王審判台前,人與夜叉鬼卒在形體與顏色上的強烈對比,背景中延燒的大紅烈火;無間地獄中被惡鬼與巨龍放入口中、被尖牙啃食,或者被利刃長矛穿刺的扭曲身體,更不用提放在砧板上剁成兩半、丟入油鍋滾燙、捆在燒紅鐵柱上、以巨石壓扁種種酷刑,這種種都讓作為觀看者的我,有種必須微微扭動關節、繃緊臉頰與眉頭,或者搖搖頭、甩甩手的不適感。黝暗的通道更無疑讓這些打了燈光的圖像更明確標示出觀者的視覺焦點,也確實收攏了觀賞者的注意力資源,當轉過頭去所能見到的只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摸著蜿蜒通道行走的觀看者也就僅能一個光源一個光源地注視眼前的地獄景觀。那麼,我們怎麼理解另一群觀賞者跟我截然不同的情緒反應呢?這得要從由上到下的訊息處理歷程說起了。
訊息處理的雙向歷程
感知的訊息處理歷程總是雙向的,以視知覺來說,前面所提過的臉孔辨識、形狀、色彩等等,都是由網膜將訊息經視神經往大腦傳送,由下往上的處理,然而大腦也需要同時由上往下,將進來的視覺訊號與過往的經驗資訊相對比,以判讀目前視覺經驗的意義為何。也因此,關於外在世界的內在表徵,所需要的資訊遠大於眼睛直接接收到的視覺訊息,而那些多出來的資訊就是由腦部,由上往下的歷程所創造出來的(黃榮村譯,2021:248)。內在表徵絕對不只是網膜在腦部的投影而已。
肯德爾認為,由下往上的訊息處理,因為都是依賴視覺與神經系統,這部分是內建的生理機制,對大多數觀看者而言都是雷同的;但是由上往下的訊息處理,則依賴個人過往經驗所形塑出的認知基模與背景知識,這對每位觀看者而言,則會有個別差異(黃榮村譯,2021:312)。就由上往下的歷程而言,肯德爾將討論焦點放在記憶的心理與生理機制上。

在場、呈現與再現的三元關係
關於視知覺由上往下的訊息處裡歷程,也讓我們必須更進一步追究關於宗教媒介物的知識論性質,這也正是宗教圖像與一般藝術圖像的根本差異。媒介特別是圖像,在Jurczyk等人(2023)由內在表徵超越的脈絡來看,首先會涉及到用來表徵的媒介或圖像是呈現(presentation)、抑或是再現(representation)了神聖?而無論是呈現,抑或再現,背後則都指認了不同型態的在場(presence)。
神聖的在場,如果借用海德格的語言,顯然不只是物理意義上的佔據空間,或者僅是及手的(being-at-hand)。如此本質性存在的呈現,就讓圖像與媒介物,不僅是參照性的、或者檔案功能的,而似乎是一種有強化功能的呈現,不單表徵了超越,而是試圖連結或等同於超越(Jurczyk, etc., 2023)。
再現則預設了在場的無可呈現,也因此其前綴詞:再,就意味著某種剩餘,對於超越的表徵與再現總有未竟之處,也總是能「再」次再現。這樣的再現也涉及到時間性的超越,原來未在場者,因為再現而得以在場,也因此再現有其特殊的時間維度。圖像作為一種關乎在場、呈現與再現三元關係的展示,在時間上難以標示起點與終點,而在意義上,則總是關乎展演跟體驗(Jurczyk, etc., 2023)。
呈現與再現的交互關係,就地獄極樂巡遊的觀賞者而言,顯得相對清晰。地獄圖像就直接呈現了關於死後世界、地獄與輪迴的論述,呈現且刻意透過浮凸的圖像與豔麗的色彩強化了熊熊烈火與人在其中的無盡折磨,地獄圖像展示出的是強化的呈現效果。在阿修羅道之後,通過陰暗曲折的走道,暈黃燈光照亮的菩薩照像,就在圖像前有著類似香案的小桌,可以擺放供品,而到了西方三聖圖,則香案上另增兩盞燈具,直接照亮左右的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居中的阿彌陀佛因為距離光源稍遠,更多是在光暈壟罩之中,而無法一眼看清,藉著強化曖昧性而漸次加強對超越的再現,如此的表徵既是一種超越性的、有所虧缺的在場,其圖像就藉著光源朦朧曖昧而未能一眼望盡,其跨越時間的臨在也僅能在光影錯雜之間得到暫時的表徵。
地獄巡遊中詮釋現象學與認知心理學的交會
對於神聖的在場與顯現的揭露,讓我們從視知覺的心理學分析,轉進到現象學的範疇。宗教媒介物對於在場的揭露,也讓我們不單純停留在以宗教圖像為分析客體的科學心理學工作範圍。最後,或許我們可以思索所謂巡遊,其實也提示我們對於藝術的觀看,或者對於地獄圖像的遊賞,是如高達美所言,必須肯認藝術中的遊戲要素,這樣的遊戲帶有不具運動目的的活動空間,並且要求旁人的共同參與,而無論參與的姿態或位置如何,作品的同一性都在參與遊戲的交往行動中被指認出來(鄭湧譯,2018)。
於是,地獄圖像的各種觀看者作為巡遊的共同參與者,就一起成為遊戲體驗的組成部件,而這樣的體驗,以及針對如此體驗的反思也回過頭來反饋出地獄概念的某種同一性。關於體驗的反思總是不確定且不一致的,因為這同樣涉及到由上到下的訊息處理,以詮釋學的話來說,這牽涉到參照體系,亦即前理解的差異,有趣的是,關於這種參照體系所造成的不確定,我們如何指稱?高達美將此稱為「記憶的保存」(鄭湧譯,2018),是的,恰恰好也是肯德爾在由上而下歷程中所關注的焦點,記憶。在這裡,詮釋現象學又再次與視知覺心理學交會了。
後記
離開東長寺後,我又搭上空港線地鐵,打算搭到下一站中洲川端站,到出口大樓七樓的亞洲美術博物館裡喝杯咖啡。點好咖啡茶點,卻見到正對著咖啡館的整個牆面,正展示著泰國藝術家Panya Vijinthanasarn,題為「魂之旅」,同樣也是將地獄與極樂世界並列的巨幅畫作。[4]面對作品右側是佛陀凝視著兩個大圓,圓中分別展示了極樂淨土與混沌血紅的地獄,極樂淨土背景是深藍與墨黑,線條工整、大大小小安坐於蓮花寶座的佛像秩序井然的由外圍往圓心匯聚。地獄圖則呈現出乍看是血色與肉色的色塊,但仔細端詳則會看到睜大眼睛、張大嘴巴的巨獸正盯著觀賞者,地獄圖中少不了的扭曲軀幹以煙塵,或者像是在這各種管路中飛散流動液狀物寫意地描繪,然而湊近看就會找到殘缺的軀體和各種不成人形的骸骨。畫作完成的時間是2001年,藝術家所描繪的地獄實則是那年美國遭受恐怖攻擊的人間煉獄。很顯然,在這個作品裡的地獄正是你我棲居的人間。
於是,關於地獄或天堂,或許不只是信不信由你,它們總是位於文化心理的深處,時不時地在道德系譜中湧現,成為我們評價、反思,以各種方式傳遞下去的文化元件(Peters, 2021)。從大佛座下到美術館裡,關於地獄與極樂巡遊,或許最終是要提醒我們彼岸不需去到某個遠方找尋,而就在眼前當下,在這個由你我共同構築的世界中。
註腳
[1] https://www.nbfox.com/self-portrait-with-striped-armlets/
[2] 這個處理歷程是由五個系統構成的階層性網路,先是臉型辨識,第二是辨識他人的身體行動,第三是分析身體運動以解釋他人的意圖,第四則藉由鏡像神經元,模仿他人行動,第五則與心智理論有關,於此理解他人的心智狀態(黃榮村譯,2021:404)
[3] 因為東長寺內禁止攝影,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上網搜尋,或者參考這個網站。
[4] https://faam.city.fukuoka.lg.jp/en/collections/6759/
參考文獻
黃榮村譯(2021)。啟示的年代:在藝術、心智、大腦中探尋潛意識的奧秘—從維也納1900到現代。新北市:聯經。(肯德爾 Eric R. Kandel,2012)
鄭湧譯(2018)。美的現實性:藝術作為遊戲、表徵和節慶(高達美 Hans-Georg Gadamer,1977)
Jurczyk, T., Krech, V., Radermacher, M., & Stünkel, K. M. (2023). Introduction: On the Relations of Religion and Images. Entangled Religions, 14(5).
Launonen, L. (2022). Hell and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Christianity. Theology and Science, 20(2), 193-208.
Peters, M. A. (2021). Hell as education: From place to state of being? Hell, Hades, Tartarus, Gehinnom.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53(4), 320-322.
Shariff, A. and Norenzayan, A. (2011). Mean Gods Make Good People: Different Views of God Predict Cheating Behavi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21(2), 85–96.
Shariff A.F., Rhemtulla M. (2012). Divergent Effects of Beliefs in Heaven and Hell on National Crime Rates. PLoS ONE 7(6): e39048.